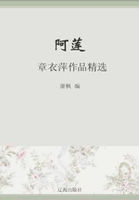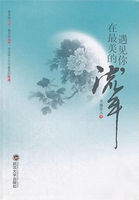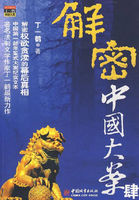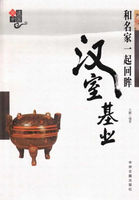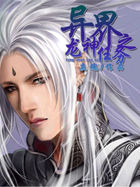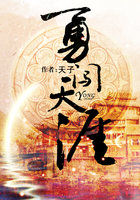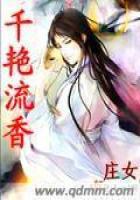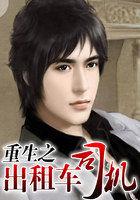王任叔,又名巴人,1901年出生于浙江奉化西南边境的大堰村,1972年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他是浙东大地上成长起来的著名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深受浙东文化精神熏陶的王任叔,一生积极参加进步斗争,虽生活坎坷,但仍保持了旺盛的理性进取精神,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以及印尼史研究等多个领域也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文学创作方面,王任叔从新诗写作起步,后写长短篇小说,成就很大。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方面,他在建设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方面,有比较大的思想贡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写人情、表现人性的理论,对解放人的思想、启迪人的思维,完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都有值得重视的思想贡献,值得深入发掘。总体来看,人们对王任叔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不够,评价偏低。
要把握王任叔的文学观念最主要的是应该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和发展来把握。王任叔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毛泽东思想,将之运用到对文艺创作、文艺现象和文艺问题等的批评和研究中去,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认识王任叔的文学观念时,需要注意到鲁迅先生的创作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积极参与的革命斗争实践和文学创作实践对其文学观念的制约。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应该特别注意世界文学中革命进步文艺对他的启迪。下文,我们将在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大体梳理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概况,为进一步总结他所接受的世界文学影响打下基础。
一 留学日本夯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础
王任叔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深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的结果。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的高峰期,1922年,他最初发表了自己的诗作。走上文坛不久,他结识了茅盾和郑振铎,并由郑振铎介绍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在“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下,走上探索人生和参加革命的路【2】。王任叔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过程中,鲁迅就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8年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之际,王任叔写了《我与鲁迅的关涉》一文,叙述了近二十年中自己对鲁迅的理解和交往的过程:他第一次读《狂人日记》,“首先给我的是一种深重的压力和清新的气息”,“鲁迅”这个名字深深印入青年王任叔的脑际,“从此我的生命仿佛不能和这两个字分离了”。之后,他看到了北京《晨报》上的《阿Q正传》,接着,读了《语丝》上登载的鲁迅杂文,更加佩服先生学问的赅博与精深。1926年他去广东时,较完整地读了《呐喊》、《坟》等著作;到了广州,有机会听了鲁迅的演讲,看到了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一面。他写了《鲁迅的〈彷徨〉》这篇鲁迅小说研究的早期论文,1930年被李何林收入《论鲁迅》一书,至今还是鲁迅研究史的一篇重要文献。
在后来参加追求进步的革命斗争中,他看到人民大众的不幸和苦痛。当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他“从革命的潜流浮了上来,又想搞文艺了”。“在我的认识上,那怕还是不自觉的吧,总以为,革命工作是为人民大众的,而革命文学却是为自己发发牢骚和不满的,名义上说是为大众,实际上却是为自己——想做个革命文学家。”【3】这段话可以概括王任叔在1927年时的思想。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他开始纠正了文艺理论上强调自我的偏颇。在文学倾向上,他同情于太阳社,但在作品的鉴赏上,却继续信从受太阳社和创造社攻击的鲁迅。他认为,想象的虚构若不从真实的基础出发,那所留下的只是空的倾向。当时他写了《革命文学的我见》一文,尽管还不成熟,但已经显示了他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观。他写道:“我们要认定革命文学并不是仅仅表现一种激昂慷慨的精神的作品,而尤其不是仅仅呼唤几句‘爱国爱国’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的,与只高喊手枪炸弹杀杀杀的作品——固然,革命文学也不必一定要避手枪、炸弹的叙述。”针对李初梨提出的“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的观点,王任叔认为:“我们应该认清文学的宣传,不是一般的宣传。它是一种‘思想的传染’,而且深刻地、比任何文字的力量来的大。所以,我总以为革命文学不是‘狂暴的煽动’,而是‘深刻的传染’;前者,是激动读者的感情的,后者,是锻炼读者的感情的。”因此,“革命文学是使读者于认识生活中去决定或理解生活之创造”【4】。这些观点既阐明了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又深刻地说明了文艺的特殊功能,与鲁迅的观点一致。因此,王任叔从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学运动走上文学道路开始,就深刻地受到了鲁迅先生的影响。正是在鲁迅的深刻影响下,他形成了比较科学的文艺观念,后来在革命斗争实践的影响下又接受了革命文学观念,同时又因鲁迅先生的影响而没有走向极端片面,最终进一步形成了自己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念。
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使王任叔意识到了自己在文艺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因对创造性的朋友们在革命文艺理论方面的娴熟非常欣赏,1929年1月他也去日本留学,研究普罗文学和社会科学。他在日本时间不长,约十个月,可是收获不小。起初他住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小镇上,请了一个日本人教日语。他学习很刻苦,几个月后,就能读日文版的《毁灭》了。后来进早稻田大学学习,同时参加留日中国学生中共组织的社会研究会,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在此期间,他还从日文转译了苏联作家克理各理衣夫的《苏联女教师日记》,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岩藤雪夫的中篇小说《铁》。此外,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一个陌生人》、《出版家》和以东留革命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这样的一个晚上》等等。在日本的学习和创作对王任叔的文艺观念影响很大。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日本和苏联进步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使王任叔所接受的鲁迅文艺观念进一步走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方向。1930年日本留学归来后,王任叔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一直未断。1935年他在南京参加世界语小组和读书会,还在读书会上给进步同志们主讲苏联李昂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5】
1935年以后,王任叔在创作小说的同时,经常为《申报·自由谈》、《申报·文艺周刊》和《时事新报·青光》等报纸撰写文艺短论。1936年,他选了14篇,取名《常识以下》由上海多样社出版。初印1500册,很快售罄。出版者无力再版,只得将纸版交给作者,算作报酬。这部文艺短论集虽然是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它是王任叔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解释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唐弢先生的评价非常准确:“这些正是他后来撰写上下册《文学读本》——以及终于修改成为《文学论稿》的思想的碎金。文章固然采用随笔式短小形式,谈的却是正面的文艺创作问题,在内容上,有点近于‘论’,而不是‘感’了。”【6】综观全书,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1.关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问题
王任叔常常说:无以为人,何以为文。在《人,作品与批评》一文中,他一开始就指出:作品“没有不渗透作者底人格的。作者底人格在作品里越渗透得越深切,那作品便也越使人感动。同时,那作者底人格底社会性越大,那么,被其人格所渗透的作品底价值也越高”。这说明了文艺工作者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性。针对当时文坛上“忠实于主观”与“忠实于客观”两种对立文艺观的反映,王任叔又在《作家与世界观》里分别批评了前一种观点的错误和后一种观点的偏颇之处,指出:“作品底创作实践,是应在现实主义下将方法与世界观统一起来的。”这就从思想上划清了唯物主义能动论与唯心主义以及机械唯物论之间的界限。文艺工作者应该反对“定命论”——历史唯心主义,抱有正确的宇宙观,可以成为“时代的先知”(《论文学作品中之定命论思想》)。
2.关于艺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问题
日本理论界曾经有过一场关于艺术价值问题的论争。一方认为文学艺术有绝对的永久的价值,另一方认为艺术只有社会或政治的价值。这场争论在中国左翼文坛也有所反应。王任叔通过“为什么古典的作品,现在的人还那么欢喜传诵的问题的论述,说出了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他说:艺术的价值无所谓永久的,那艺术的价值,是要看它发生的社会,与后来社会底适应程度如何,而且随时随地随人在变易的。但又统一于相应的社会里的”。“迷信艺术文学有绝对的永久性”,“或根本否认它那适应某一特定社会的本身价值”,都是错误的(《从怀古谈起》)。
3.关于文学典型问题
什么是典型?作者认为,一方面是现实社会里常见的,另一方面又确实具有他自己所属社会层的一切特性。他列举鲁迅笔下的阿Q、果戈理小说里的人物加以说明。他在《典型的写出》中写道:“典型人物底写出,却还是有赖于个性之社会学的发见。??个性之社会化,和从普遍性中抽象出来的特殊性底映出。”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创作论和文艺观的。
王任叔的这本文艺短论篇幅不多,印数也少,但书中涉及的问题却不少,并且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过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