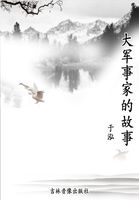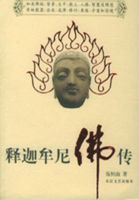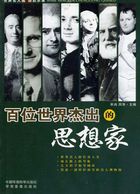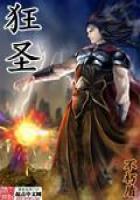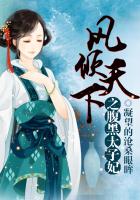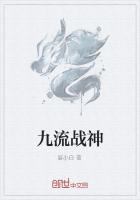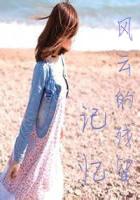又一次离别的时分,他忽然问她:“地球上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
她飞快地回答:“便是我站着的地方。”
冰雪聪明的你,既然什么都明白,那么你还有什么不放心?我是飞入你手心的雪花,在你面前我没有自己。高君宇默默地想着,又一次走向了风雪的长途。
满山红叶寄相思
1925年新年后不久,高君宇约着石评梅同游雪后陶然亭,两人沿着城墙根慢慢走着,君宇忽地蹲下身去,在雪地上写下评梅的小名:心珠,对着字迹痴痴看了半天,评梅不好意思起来,便问他:毁掉么?君宇勉强点了点头,评梅却又放过这两个字,兀自往前走了。
他帮他拿着线团,她低头静静织着线衣,他望着她,心中有千言万语,最终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只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了握她细瘦的手腕:命运是我们手中的泥,我们将它团成什么样子,它就得成什么样子。
彼时他们谁都不知晓,高君宇的生命,已经要开始倒计时了。
数年辛劳,风霜雨雪,已经极大地损害了高君宇的健康。待石评梅接到消息赶到医院时,躺在病床上的高君宇已然形容枯槁,再看不出那个风华正茂、清俊儒雅的好青年的样子。评梅忍不住低低地啜泣了起来,君宇深陷的眼眶也变红了,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仿佛这个动作都要花费他很大力气:“珠!什么时候你的泪才流完呢?”评梅的热泪更是止不住了,只怕你的病好了,我的泪才能收一收呢。可是,可是……
评梅不敢再想下去了。她蓦地跪在君宇的病榻前,赌咒发誓一样地说:“辛,你如仅仅是承受我的心时,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你若真的爱我时,我知道你也能完成我的(独身)主义……从此后我为了爱独身的,你也为了爱独身。”
君宇苦笑起来,这个倔强又死心眼的小女人啊,然此情此景,此时此刻,他更不会与评梅争辩什么,他明白她,甚至比明白自己还要深刻:“珠!放心。我原谅你,至死我也能了解你,我不原谅你时我不会这样缠绵地爱你了。但是,珠!一颗心的颁赐,不是病和死可以换来的……珠!我就是死后,我也是敬爱你的,你放心!”
评梅说不出话,只是默默垂泪,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她的心,其实早在奉还那枚红叶时,就已经全然地付托与他了。
高君宇的病情日渐恶化了,评梅下了课就往医院跑。三月四日下午,评梅又去看了君宇,回来后越到晚间,越是心神不安,她甚至有冲动跑到君宇面前,告诉他只要他不死,自己什么都愿意牺牲,只要他能好好的。半睡半醒间,忽然看见君宇含笑站在面前,穿一身黑色西装,大红领结,手中还执了一枝白梅。评梅大叫一声,猛然醒来,心跳如擂鼓——那时已是半夜两三点钟了,只等快快天亮,她要赶快冲往医院!
临行前,他在这个世上最放不下的还是她吧,所以特地来向她做个告别。时年,高君宇29岁。
碧海青天无限路
几度晕厥,又几度醒来,先行的人走了,独留世间的人这样悲摧痛心。整理君宇的遗物时,石评梅又发现了那枚红叶,两人的墨迹依然如故,只是叶子中间裂了一道缝,评梅的心霎时也碎了。她伸出抖颤的手拿起这枚叶子,从未有一个时刻这样深刻而明白地意识到:曾经拒绝了他的自己,原来是这样深沉地爱着他。评梅锥心泣血,一遍一遍在心中嚎泣着追问自己:你那时柔情似水,为什么不能温暖了我心如铁?
在高君宇的追悼会上,评梅的挽联最为简短,“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深谙古诗词典故的评梅,何尝不是在抒发自己“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无限悔恨呢?
遵从他的意愿,高君宇的墓,就立在陶然亭畔,这是他们相会的地方,也是无数有志青年战斗过的地方。
评梅提起笔来,亲自为君宇题写碑文: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从此,陶然亭的明月,陶然亭的晚霞,陶然亭的池塘芦花,都将是他的伙伴。
她一遍一遍地踯躅于坟前,心头满是无声的哀歌:想追回昔日光灿的容颜,祭献在你碧草如茵的墓旁,可青春的残花,毕竟已随你一同殉葬。
想吻遍你墓头的青草在日落黄昏,哪怕是梦啊,多想再见见你不屈的英魂。
梦中我低低唤遍了你的名字,醒来却只见窗外长空孤雁哀鸣。
在这腥膻遍地狼犬当道的世间,唯有想起你时方有一霎的甘甜。愿乘黄鹤度虹桥,在无垠之中与你永远的相逢。
星月满天时,将你遗我的宝剑双手高擎,美人不如玉,剑气更长虹。愿同你统统埋葬,这英雄儿女的热情。
满腔辛酸与谁道?愿此恨吐向晴空将天地包。我爱,期你如彗星照亮天地,期你用火花焚烧浓黑。
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饮。醉卧在你的墓碑旁,任霜露沾湿我衣襟。从此我再不醒,再不醒…………
独留青冢向春风
从此,评梅的案头总放着一个银框,里面是君宇的遗照。相前放着一个紫玉花瓶,瓶中供着白色的玉簪,清芬如缕,幽幽萦绕。不是因为想他时才看他,而是因为看他时反而是莫大的安慰。
有时,她也会想起《楞严经》中的句子,“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爱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需在缠缚。”是了,她欠他的,他予她的,且慢慢纠缠下去吧。
君宇,他是她生命的盾牌;更是她灵魂的主宰。自他去后,评梅生命的河流,从此就是“自在的流,平静的流,流到大海的一道清泉”。生如寄,死如归,于万般哀凉之中,反感到寂静的快乐,和生命的大解脱。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她变得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战士。先后主办《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和《世界日报·蔷薇周刊》,以笔为椎,奋力刺向这浓黑的世间:纪念刘和珍、杨德群等的《痛哭和珍》、《深夜絮语》,哀悼李大钊的《断头台畔》,济南惨案发生后不久,她挥毫写下《我告诉你,母亲》:你莫过分悲痛这晚景荒凉凄清,我有四万万同胞他们都还年轻,有一日国富兵强誓将敌人擒杀!沸我热血燃我火把重兴我中华。
君宇,你看见了么?我将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只要我一息尚存。
1928年9月,高君宇去后三年,石评梅因患脑膜炎猝然离世,同一家医院,同一间病房,同一个时刻,她终于踏上了寻他的路。
死后,人们在她的日记扉页上发现她的题词: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高石之墓,几经摧毁,又几经重建,而今依然矗立在陶然亭畔,笑对春风。
在这样一个奢谈梦想、羞言信仰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说喜欢、说离去就放手的年代。有这样一份笨拙到令人叹息、羞涩到让人怜爱、保守到让人尊敬的爱情,让我们得以剥离名利权势、收入学历、长相住房等等所有外部条件,不掺杂一点杂质地,去追忆怀想一份真挚感情的本来面目,如同你梦中那位永远白衣飘飘的少年。
而那种古典式的爱情,其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连夜翻过两座山崖,将我从绝壁采来还带着露珠的野花,轻轻放在你的窗前。坐在后花园的秋千上飞起又落下,落下再飞起,只为看一眼你的马车,辚辚驶过那条青石板桥。
我们何其幸运,借着石评梅以血泪为墨真情为笔的动人抒写,隔着那虽然老旧但还未曾全然远离的岁月,得以一窥这段古典爱情的真面目。这样的爱情,此后再也不会有了。
它教我们学会珍重——珍惜每一份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情意,沉沉放在心间,做一个懂得爱人,更懂得自爱的好女子;学会成长——哪怕是以生命不可承受之失去为代价,终于含着泪带着笑领悟了爱的真谛;学会信仰——以你的理想为我的理想,以你的目标为我的目标,为了那个你向往的世界,我愿意前行再前行;学会忠诚——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人间天上,我们总会再度相逢。
不识梅郎是梅郎——梅兰芳与孟小冬
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相对于名满天下的梅老板而言,孟小冬的光辉在今天似乎黯淡了许多。也许她选择了留在她的年月里,那是她最开心的日子。
这句话是宫二对叶问说的,冥冥之中,也是孟小冬说给自己和那个人听的。天意高难问,人情纤如丝——无论是有着几分旧贵族气息的陈凯歌,还是文艺小资到无可救药的王家卫,都选择了章子怡,来扮演他们心中最为传奇的这个女子。
章子怡的孟小冬已经足够好,章子怡的宫二却更加好,除了她,简直想不出来谁能担当这个一袭黑衣素白面孔念念不忘自有回响的角色。无论在电影外的世界遭受多少非议和毁谤,沉默,转身,用作品说话,让所有喜欢和不喜欢她的人,都无法不正视她的存在。
但能称得上一代宗师的,又哪里是那么简单?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宫二看得清楚自己,也算见过天地,却始终见不到众生。叶问在他人生的春天里时,大约也体会不到何谓众生皆苦。直到后来半世颠沛,流离终老,方才成就了宗师之大。
我无法切断这种玄之又玄的联系:纵观梅兰芳一生历程,何尝不是如此?必始见自己,而后可以观照天地;必知天地之悠悠,而后方解众生之情。然囿于时代及种种因素,小冬的后半生却是戛然而止,如剑在匣中,钗还奁内。既无授徒,也未登台,一身绝艺,大半付之流水,无缘得见众生。
如若宫二见到小冬,不发一语,大约便能看出彼此眼中内敛的锋芒。风尘之中,每多如此性情之人。梨园,亦是江湖。
两枝仙桂一时芳
在这个梨园江湖中,梅兰芳是当之无愧的伶界大王。当年沪上好事者评选四大名旦时,于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三位的排序高下颇有争论,然于梅兰芳却是众口一词:其余人等皆输他一头地。四大名旦之首,非尔其谁?
与程派之幽咽婉转、荀派之伶俐尖新、尚派之俊爽清健相比,梅派的艺术特色,很难一言以蔽之。即使以梅兰芳本人的天资、勤奋与种种不可再得的因缘际遇,也要用了小半生的时间,方可开宗立派。概而言之,可谓“集大成”,如花中牡丹,鸟中凤凰,自是标格天成,又可谓“正宗”,如书学颜体,诗学老杜,总是没有错的。
但若以为梅派艳丽而少回味,却是大错特错了。当年梅老板初见福芝芳时,觉得这个女孩子“天然妙目,正大仙容”,是个端庄有福气的模样。他自己的扮相却是偏清丽雅秀一路的,于雍容大度外,别有韵致万千。也因此特别得当时文人雅士的追捧。在他们心中,梅兰一类“冷色调”的花,格调自是高过热闹纷繁的桃杏一路的。哪怕是清高自许到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西风误呢,总好过轻薄桃花追水流不是么?“不如桃李,犹解嫁东风”云云,这话却只能从反面来看了。
所以梅兰芳最为脍炙人口的古装新编剧中,无论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洛神,奴今葬花人笑痴的黛玉,吴宫空自忆儿家的西施,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的虞姬,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嫦娥。眉目中都有着清泠泠的、距离世俗不远不近的冷艳——却偏偏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那样的形容,大约如曹雪芹形容绝代佳人警幻仙子之妹,“鲜艳妩媚,大似宝钗;风流袅娜,又如黛玉”,可谓“兼美”。当年名动京城的梅兰芳,也可称得上这兼美二字。
观梅派名剧《贵妃醉酒》,杨贵妃之国色天香自是人所共知,真个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看她手执宫扇,在宫娥簇拥下款款行来——这样一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美人儿,却有一颗敏感而柔软的心灵:海岛冰轮的月色,跃出水面的鲤鱼,轻落花荫的大雁……唯其如此,方知鲜艳妩媚为其表,灵心慧质是其里。又看她扇舞障面,醉步摇摇,衔杯饮酒,折枝嗅花,一个卧鱼身段,款款向后仰下身去,直到与台平齐,满头珠翠却是分毫不乱,端的是仪态万方,媚而不妖,且真真是贵妃的范儿,起舞弄清影,不似在人间呢。
这出戏,冷中有热,热中有冷,热的是人世间的情爱,冷的是出离于人世间情爱的悲悯观照——梅兰芳以浓艳繁华到了极致的表演,烘托出了淡极始知花更艳的境界,后辈谁人能及呢?
今日的梅派传人,更是大多只偏了鲜艳妩媚雍容端庄一路,美则美矣,总嫌稍欠回味,也难怪自诩懂戏之人要偏爱程派了——想当年,梅兰芳的“相”能够独树一帜艳压群芳,其他三旦瞠乎其后,又岂止是表面上的色相那样简单?
孟小冬亦自有她的好处,以妙龄少女,饰髯口老生,偏偏天衣无缝令人叫绝。老生本就是内敛深沉的路子,忍辱负重如程婴,璞玉浑金如莫成,千般思量如杨四郎,老谋深算如薛平贵。经她天生祖师爷赏饭吃的、毫无雌音的金嗓子一加演绎,真真是一唱再三叹,慷慨有余哀。小冬又生得极美,哪怕是在黯淡的黑白色照片里,她的风华都要喷薄而出:一双妙目清凌锐利,如秋水寒星,又是白水银里养了两丸黑水银。且生得一管好鼻子,所谓的鼻如悬胆风骨崚嶒,唇线分明的菱角嘴却兀自紧紧抿着。这样的英丽不凡,思来想去,也唯有“烟分顶上三分绿,剑截眸中一寸光”两句可以形容,她比甄嬛更适合这样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