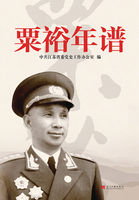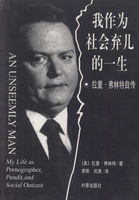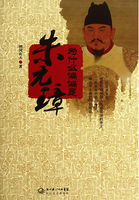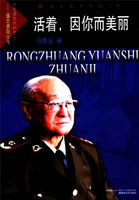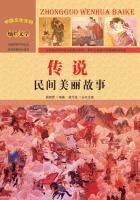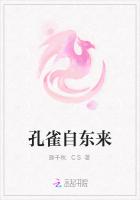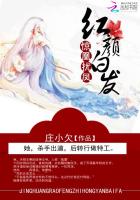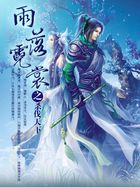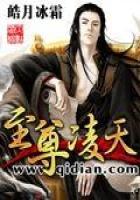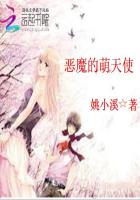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字其人。灵心慧质的“四妹妹”张充和,用十六字写尽他一生风华变迁。
然而他最爱他的黑凤,三三,三姐,小妈妈,乌金墨玉——张兆和。
荒漠世间,红尘万里,得你携手相伴,共度一生,于愿足矣。
许我,许我喝一杯甜酒吧
1929年,27岁的大作家沈从文喜欢上了19岁的小女生张兆和,当时,他是她的老师。
小女生眉目俏丽,短发齐耳,是个不折不扣的黑美人,颇有几分当年米雪和林凤娇的神采,更多几分世家子的落落大方。张家有女兮,从者如云;虽则如云兮,匪我思存。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她自己也不晓得,可这位古怪而倔强的沈老师啊,一上来就是无保留的热情和痴狂,她害怕了,退缩了,本能的反应就是拒绝。
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得越急,一个跑得越快。
小女生气愤愤地冲进校长胡适之先生的办公室,掏出沈从文写给她的情书:“这是一位老师该对学生说的话吗?”胡适却慢条斯理地推推眼镜,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开口,先夸起了沈从文的无双才华。
最后,他对面前的小女生说:“他顽固地爱着你。”
小女生甩甩短发:“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蹙了眉头,面前这个混沌未开、稚拙别扭的大小姐,真是自己那个老友的良配么?一个是江南烟雨洗出的洁净女儿,一个是胸中自有千山万水的湘西蛮子,这两个人真的合适么?适之先生大摇其首,转而劝阻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
沈从文仍然不管不顾,一意付出,不问前程。三年坚持,情书数百。她从排斥到愧疚,从愧疚到感怀,从感怀到心动。终于,她头一次抬起头直视他的眼睛,甜蜜地微微笑了。
当时,他30岁,她22岁。
他在写给她的信中悠然喟叹:“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白云一样悠远,明月一样洁净,没有人能不为之心动,没有人。
暑假,回湘西老家前,他先去苏州她的家中拜访她,紧张得手脚没放处,却仍然记得讨好她的每个家人。终于,她的父亲点了头,姐姐发了话,弟弟给他买了冰棍。
她去邮局给他发了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一条河流的爱情
1933年,伊人终于走下神坛,成了沈从文的妻子。第二年,沈从文回老家探望母亲,张兆和留在北平等他归来。
长途归舟,湖山失色,他将思念化作一行行清丽如雨中丁香的文字,托鸿雁穿行千里云天,好让那忧愁的小妻子看见。
他把这些都写入了《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之中,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关于爱情、关于故乡的不朽绝唱。
兆和惦念他:“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这风,我很发愁。”
从文宽慰她:“一个人心中倘若有个爱人,心中暖得很,全身就冻得结冰也不碍事的。”
有情饮水饱,这些甜蜜的傻话,也只有有情人写来才甘之如饴。
十多年前,沈从文也坐着这样的小船,懵懵懂懂地出了湘西,身边是水手们玩牌打闹的嘈杂声。今天他又坐着小船,回味着一切的过去,“想着远远的一个温和美丽的脸儿,且这个黑脸的人儿,在另一处又如何悬念着我!我的命运真太可玩味了。”
“一切过去的种种,它的结局皆在把我推到你身边心上,你的一切过去也皆在把我拉进你身边心上。这真是命运。”
满怀感恩敬畏,他要用手中这不属于人间的妙笔来告诉妻子,这千里长途中的无上美景。
河水已平,水流渐缓,两岸小山皆接连如佛珠,触目苍翠如江南的五月。在河边的吊脚楼里,灯光烁烁,落到水里,像晃动的星子。声音同灯光的所在处,必定有极为动人的画图。船主在喝酒取乐,随旁的妇人手上戴有镀金戒指。极世俗又极深远,极鲜亮又极悲伤。
这是画图。
在舟中,还能听见水面人语声,橹桨搅水声,水手天真烂漫的骂声,又美又凄凉的军队的号音……
还有橹歌声,同滩水相应和,声音雍容典雅之至。
那橹歌的内容,或许是这样子的:要来就快来,莫在后面捱,呵……
或许是:风快发,风快发,吹得满江起白花,呵……
或许是: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满江的橹歌,轻重急徐,各不相同,又复谐和成韵。
这是声音。
凡是在这条河里的一切,无一不是这样把恐怖、新奇同美丽揉和而成的调子。对于这条河,他虔诚地膜拜:“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河流是他的母亲,而兆和是他的缪斯:“倘若要我一个人去生活,作什么皆无趣味,无意思。我简直已不像个能够独立生活下去的人。你已变成我的一部分,属于血肉、精神一部分。”
这条长河,盛满了他的爱情。一条河的爱情,毫无渣滓,透明烛照;而到深潭急流处,又像火一样热情。这是他对她的爱情。
在梦里,在梦里见过你
沈从文把自己的女神糅进了作品中,《长河》中的夭夭,《边城》中的翠翠,都有着兆和的影子。“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
这应当是沈从文的梦想中,完美女子的模样,兆和像她,但又不完全是她。现实中哪有这样自然的女儿呢?尤其是婚后,两个人的书画琴棋诗酒花,必然要加入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君不见精灵古怪的蓉儿,都变成了为儿女忧心忡忡的中年妇人么?
沈从文失望了,苦闷了,便在这时,另一位文艺女青年高青子出现在两人的生活中。伊云英未嫁、浪漫多情,第二次见面,便特特换上了“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这恰恰是沈从文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
伊人手段真真高明,须知文人最受不得这种毫无掩饰的仰慕和向往,而化身为他的书中人,更让他有一种聊斋里书生遇仙般的梦幻之感。毫不意外地,他向高青子投去了“青眼”。
这段“婚外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最多只是一次精神领域的动荡和出轨,过程也只有在沈从文当时的散文和小说中略见端倪。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他们的婚姻生活,在经历了短暂的波折后还是继续走了下去。
“人生的理想,是感情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十分明显。
他们陆续生了两个儿子,龙朱和虎雏,像月下的篝火,有种原始而天真的动人力量。也是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名字。现实和梦幻,在沈从文这里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
战火起了,山河碎了,那原本不解世事的大小姐,不知不觉已蜕变成一位无所畏惧的母亲。而沈从文的心中,却永远有一个超人间的边城世界。
他先逃难去了昆明,她和两个儿子(当时虎雏刚刚出生两个月)暂时留在北平,事事皆须亲自料理。她在写给他的信中说:“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这是女人,在生活面前一夜长大的女人。
而她的男人还在孩子气地抱怨:“你爱我,与其说爱我的为人,还不如说是爱我的写信。”不然,为什么不同他一起千里逃难呢?
美丽,总是令人忧愁
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感性与理性时而战争,时而妥协,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对方的血肉、感情和生命,成为彼此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