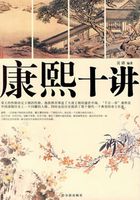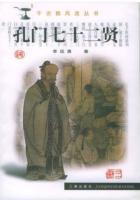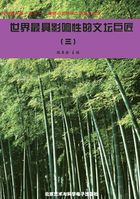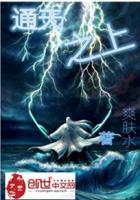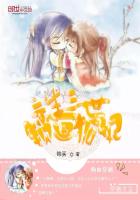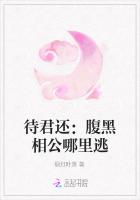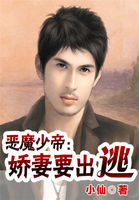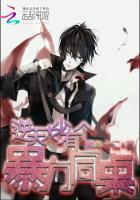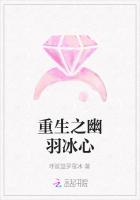可到了像她和周有光那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境界,又有什么需要昭告天下的呢?所以这种倔强的、少女般的深情,愈发让人动心。首先,我们能够看到,被爱情悉心滋养了一生的女人,能够葆有怎样动人的美丽。再来就是,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磨折、困难侵袭,她仍然能够做到“不妥协、不盲从”,这更是仅属于真正中国知识分子的、“士”的品格。
看张家四姐妹年轻时的合影,春兰秋菊,各具风采。更妙的是她们之间的相互辉映和衬托,愈发让人觉得如行山阴道中,山水清景,扑面而来,教人目不暇接。
而在其中,我私心最为偏爱的,就是清丽如菊的允和,从这一点而言,我和周有光老先生非常有共同语言。
1925年,16岁的张允和还在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读书,同学中有一位叫周俊人的小姑娘,两家大人都是熟识,因此下一代的来往也十分密切。但一直到1927年她考入中国公学之后,周俊人“心怀鬼胎”的哥哥周有光,才托家中姊妹交给张允和第一封信。
收到信的张允和惊慌失措,一时间大乱方寸,她拿着信去向年长的女同学请教。同学果然老成,满不在意地告诉她:“这有什么稀奇,人家规规矩矩写信给你,你不写回信反而不好。”
两个人的通信正式开始了,信中可以无话不谈,真等到暑假见面时,两人却不似往常相处那样自然了,周有光的手脚没处安放,张允和老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衣角。
他们都心知肚明,有一种崭新的、奇妙的东西诞生了,旧日两小无猜的时光,永远被葬在了岁月的深处。
60年后,已经年近八旬的张兆和老太太,凝望着身边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老伴,眼中仍有温柔的光,初恋的每一个细节,在他们的心中仍然清晰有如昨日。
那是在1928年某个秋日的黄昏,两个人从学校大门慢慢走出来,到吴淞江边的石堤上去散步,天上正飘着些微云,地上正吹着些微风。微风吹动了他们的头发,教少年人的心啊,怎么能不盛放如花?
沿着石堤走了很久,他们在一块平整的大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手帕铺到石头上,手帕不大,两个人不得不坐得很近。于是他轻轻地抓住了她的手,她很紧张,手心微微出了汗,他连忙又取出一块洁净的白手帕,塞到两只手中间。她反倒又乐起来了:这人的手帕可真多。
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可是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以后,不是一个人寂寞的走路,而是两个人共同去探索行程。不管是欢乐,还是悲愁,两人一同负担;不管是海浪险波,不管是风吹雨打,都要一同接受人间的苦难,更远享受人间的和谐的幸福生活!
这一刻,是人生的开始,是人类的开始,是世界的开始,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刻。
这一刻,是两个人携手跨入了人生旅途。不管风风雨雨、波波浪浪;不管路远滩险、关山万重,也难不了两个人的意志。仰望着蓝天,蔚蓝的天空,有多少人生事业的问题要探索;面对着大海,无边的大海,有多少海程要走啊。
这一刻,天和海都似乎看不见了,只有石头既轻软又温柔。不是没有风,但是没有风;不是没有云,但是没有云。风云不在这两颗心上。一切都化为乌有,只有两颗心在颤动着。
张允和《温柔的防浪石堤》
这是老辈人的爱情,一旦牵了手,就是一生一世的允诺。水来,在水里等你;火来,在火里等你。活着,为你操持家事遮蔽风雨;死了,不喝孟婆汤,在奈何桥头等到你。
我们还有这样的勇气和决心吗?他们的情意柔韧如丝,我们的好感轻薄如纸。春蚕到死丝方尽,但只要外界一星半点儿异样火苗,这张纸就瞬间化灰化烟了。
结婚要趁早啊,不然不痛快
1931年,允和到杭州的浙江大学借读,周有光恰巧也在杭州教书,两人陷入热恋。不见时一日三秋,见面时三秋一日,好容易等到允和毕业,1933年,两人就迫不及待地结婚了。
年轻人主张新事新办,家中的老辈人却坚持要选个黄道吉日。几经改动,终于商定婚期后,允和的干干(保姆)又拿两个人的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煞有介事地捋着胡须:“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
张允和活到了九旬开外,周有光今年已经106岁了,但思维的敏捷程度让年轻人都自愧不如。
是不是两个本该苦命的人凑到了一起,反倒阴阳互补、否极泰来了呢?当然如此,天道虽无亲,常与有情人嘛。
两个人上演了一出80年前的“裸婚时代”,结婚前夕,周有光不无忧虑地对准新娘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
张家二姐气歪了鼻子,这不是太小看自己了么?回家去,写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给准新郎,十页纸,一句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1933年4月30日,在这场简单的婚礼上,亲朋好友见证了他们的幸福。大姐夫顾传玠一支玉笛恍若谪仙降世,小妹妹张充和一曲《佳期》恰似惊鸿照影,还有一位来自俄国的金发碧眼宁馨儿弹奏钢琴。中西结合,今古交织,真幻互映,还有比这更难忘的婚礼么?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兆和的父亲无意中发现一笔两万元的存款,于是给了她两千元当嫁妆,再加上宾客礼金,除去结婚花销后仍结余颇多。两个年轻人一商量,倒不如读万卷书兼行万里路,出国留学去也。
可一登上远洋轮船兆和就狂吐不止,吐得天昏地暗、头昏眼花,到了陆地上还是止不住,周有光担心个半死。糊涂又马虎的小夫妻到医院一检查:原来,一个小生命已经悄然来临了。
当然,看多了小言和偶像剧的姐妹们早在看到兆和大吐特吐时,就已经知道怎么回事啦,不许剧透啊。
1934年4月30日,周有光、张兆和之子周小平呱呱坠地,此时,恰是他们一周年纪念日。张兆和乐昏了头,逢人就说“我结婚那天生的孩子”,闻者皆满头黑线哭笑不得,难道新娘是出了教堂直奔医院不成?后经反复提醒,张兆和才想起来还少说一句:“第二年。”
昨夜狂风度,吹折江头树
我们看张家四姐妹的故事,总也绕不开1937年,那个悲壮而惨烈的年份。四姐妹的爱情、婚姻、生活,都在这一年前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变化。
张允和带着三岁多的儿子小平和两岁多的女儿小禾,开始了逃难生涯。周有光被工作羁绊不得脱身,清瘦娇小的允和就成了一行六七人的主心骨,上海,合肥,六安,合川,成都,重庆……光是在四川就不知搬了多少次家。辗转西南天地间,她身上爆发出的惊人能量,让全家人紧紧维系在了一起。
1941年,女儿小禾忽然说肚子疼,战争期间,缺医少药,又没能及时送到医院救治。痛苦挣扎了两个月后,小禾还是告别了爸爸妈妈和哥哥,独自飞往了天堂。
作为母亲,允和的悲痛无法形容:
我的眼泪可能流干了,这次惨痛的事件之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从没有再向人提起过这件事。
妈妈的女儿,妈妈的小棉袄,原指望这一生为你遮风挡雨,你却走在了妈妈的前面。儿想妈妈一阵风,妈妈想儿在梦中。几十年后妈妈去见你,妈妈老了,你还是妈妈的小禾。
周有光在女儿的坟前潸然泪下:
坟外一片嫩绿的草,
坟中一颗天真的心。
摸一摸,这泥土还有微微一些温暖,
听一听,这里面像有轻轻一声呻吟!
连七岁的周小平都知道,妹妹再也回不来了,“我再也看不见你了。”
小禾的离去,成为这一家三口心上永远的伤疤。
兆和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到了儿子身上,然而祸不单行,1943年,在自家院中玩耍的小平,被不知何处飞来的流弹击中了肚子。兆和眼前一片浓黑,却强撑着不敢倒下,连忙把小平送到了医院。
医生说,小平的肠子上被穿了六个洞。兆和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一直守在儿子的床前,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儿子。第四天清早,小平终于度过了危险期,丈夫也赶到了医院。兆和放松下来,想哭,却发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女儿去了,保姆也去了,儿子险遭大难,丈夫为养家糊口四处奔波,一次又一次艰难磨折,张兆和都挺了过来。我想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也应该包括她这样的女性。
兆和不是生来的铁娘子,相反却是才情俊爽的女诗人。某次逃难途中,她写过两首小诗:
其一:岁岁客天涯,夜夜梦还家。青草漫山碧,孤村月又斜。
其二:梅黄橘绿时,归期未有期。易别难成聚,花飞知不知。
清婉流丽,哀而不伤,端的是大家出身的正道。让人想起南渡之后的李清照,“如今憔悴,云鬟雪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但我想张兆和还是会笑她,未免太过消极矫情了点,人生百年,苦乐相参,为何不抬起头来,尽量向前看呢?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
新中国诞生前,周有光与张兆和环游了地球一周,这个富有浪漫气息的新旅程的开头,似乎也预示了他们后来几十年的甜蜜生活。
二姐张兆和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解放后先是当中学历史教师,针对教科书上存在的问题,她写了洋洋洒洒两万字的文章,很多质询和观点被登载在《人民日报》上。1951年,允和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这应该是一个更能发挥她长处优点的岗位,但接踵而至的“三反”“五反”运动,令允和深受打击,干脆辞职回到了家中,从此安心做起了家庭妇女。
周有光的经历更啼笑皆非一点,作为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解放前他一直在银行工作,是不折不扣的金融精英,解放后又担任上海经济研究所教授。到了1955年,却调入了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订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等有关工作。这一转行,从此就再也没回到经济学的老路上。
如此阴差阳错,反而让他逃过了“反右”一劫。而允和的急流勇退,更让她在“文革”中少受波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一个半路出家的语言学家,和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家庭主妇,开始了他们别致有趣的后半生。
两夫妻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每天夫妇俩每天上午喝一次茶,其实是红茶冲奶粉;下午喝一次咖啡,其实是咖啡冲奶粉。每天碰杯两次,从无改变。这一习惯还有个名头,叫“举杯齐眉”,举杯相似,会意一笑,多美好的一天。
允和是资深昆曲名票,吹笛度曲无所不能。著名漫画家丁聪曾给夫妻两人画过一幅漫画,画面上,周有光用三轮车载着张兆和招摇过市,有光双手扶车把,允和手捧笛子。两人皆面带笑容,丈夫慈祥宽厚,妻子慧黠通透,表情皆传神之至。见者无不捧腹,视为经典。所谓“白发老头,新潮才女”,出处就在这里。
结婚70年来,他们从未吵过架,无论是处理大家庭间的亲戚关系,还是在儿女教育问题上,两人总是和颜悦色、有商有量。因为两人都信奉一句话,“不要生气”,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在人生的大关节上,两人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些许生活小节方面,你让我三分,我敬你几寸,两老的日子竟是越过越和谐、越过越滋润。
有年轻记者满怀欣羡和不解,采访周有光老人:“您和张允和先生的爱情已成经典,有什么建议和秘诀,好传授给现在的年轻人呢?”
周老先生一语中的:“男女要爱,还要平等地相互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家庭生活才会快乐。现在青年人有爱无敬,当然吵架了……中国古代提倡举案齐眉,我提倡举杯齐眉,就会愉快……‘快餐式爱情’的问题是只有爱没有敬。”
这话在我听来,可谓振聋发聩,每一位世纪老人都是一部智慧的百科全书,何况本有“周百科”之称的老人家,更是百科中的百科。现代人口口声声说爱,却总举着爱的幌子行伤害他人之事,女生非要男朋友对自己俯首帖耳,男生希望女孩子对自己言听计从,父母强迫孩子服从自己的意愿,长辈反对晚辈脱离自己的羽翼……太多太多的负面例子,我真怀疑,他们口中的“爱”到底是爱本身,还是为了满足个人愿望和私欲的一个工具?
孔子说:“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话可以当作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准则,爱情也不例外。更可以和周有光老先生的话相互补充注解,“爱”是亲近,“敬”是适度远离,给予对方,也给予自己一定的空间和自由。把握好这个分寸,领悟到其中奥秘,大约世上会多出许多白头到老的恩爱夫妻。
周有光先生是大学者、大名人,而张允和虽然号称才女,却并无任何职务头衔在身,只是位“家庭妇女”。但周有光对太太的一切成绩和爱好,都表以十二万分的赞成支持。张家姐弟早年间曾自办家庭刊物《水》,停刊半个多世纪后,老太太张允和号召张家其他老头儿老太太一起,重新将《水》复刊,所谓“最小的杂志,最老的编辑”。就是这么点小爱好,周先生却很是推崇,老太太也傲娇地说:“我比有光还有光呢。”
夫妻做到这等境界,是爱人,也是朋友;是恩人,也是手足;是情人,也是知己。你从我眼中看到了我的世界你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从你眼中看到了你的天堂我的天堂我们的天堂。
隔花人远天涯近:张充和与傅汉思
幺妹,这个词读在口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娇娇糯糯,仿佛桂花飘香的时节,喝上一碗香香甜甜的红豆沙——连灵魂都要舒展荡漾在半空中了,像白云一样的,形状无定,任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