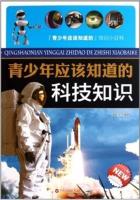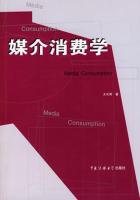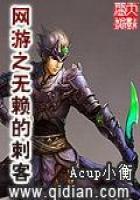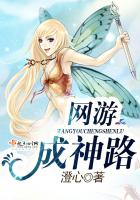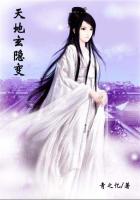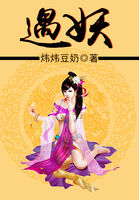街道的状况是我们的权限无法改变的,但是学校的状况却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得到改善,然而,我们并没有去努力争取到或者干脆办到,这令我很伤心!校门口破旧不堪,迎门就是建于七十年代的小三层用于教室的危楼。当然,绕过门前的危楼,你会看到相距大约二十米也有一栋同样的教室,照样破旧不堪。我不用详细介绍它们的外表是如何破旧,教室里面更是如此地配套,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情况。教室里墙壁剥落,屋顶漏雨的痕迹斑斑,上面除了四根破旧的灯管还有四个吊扇,窗户满是尘土,不过还加上了防盗用铁丝网,我开始为小偷发愁了,如果他们冒那么大的危险钻进来又能偷走什么呢?他们一定特别伤心,甚至一年里都觉得晦气。再看看上课的孩子们,那个可怜啊!一排排破桌旧凳上大多是睡得很香的孩子们,而我们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一手拿着教材,一手拿着粉笔,在那里讲个不停,有的为了放大声音还自费配备了扩音喇叭,即使这样也没有惊醒熟睡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已经非常习惯这样的睡觉环境了。难怪我们的胡燕老师向别人介绍学校的课堂改革经验时,用了一句“老师讲得大汗淋漓,学生睡得酣畅淋漓”来形容当时的情景。尽管如此,我们的学校还在搞什么青年教师示范课、汇报课等等之类的课,还专门留下一节课评课。他们轮流着说我就听,我在我的《做整个的校长》里写到:“听着听着就感觉评课座谈会变成了表扬会,赞扬的话,恭维的话一大套。谈到某老师的毛病时,话题一转,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问题需要注意。难道一个人就那么一点点需要注意的问题吗?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就算是那一点点的问题,它究竟是个什么样问题。我继续强调,同事之间也要敢于指出问题。少讲‘好’,多挑毛病。现在召开的座谈会实际上是个专家会诊,也如,外科医生为病人做肿瘤手术,如果那位医生手里拿着手术刀,欣赏着那块肿瘤大发感慨,‘哇!你看多漂亮的肿瘤啊!’与其如此,不如让它发展下去吧。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一般情况下,改革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去的办法再也不能使用了,陷入绝境,改变才可能有活路,不改简直是死路一条,这种改革最容易达成共识;另一种情况是传统的东西仍然能够使用,而且目前仍有前景,况且别人也是如此,最大的区别也无非是好些、差些。有人不在乎,他好他的,咱就这样,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你逼着他们改革他们立即火冒三丈的,却只是因为这扰乱了他们早已养成的习惯,甚至有人认为,一些改革的人是在没事找事。我就觉得,既然做了什么事情,只要认准了就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无论是谁都改变不了。
就课堂改革而言,我觉得我们的课堂谈不上改革,只不过是修改了或是改变了传统课堂而已,其实质是恢复了真实的课堂、自然的课堂、学生的课堂。最大的改变是课堂的主体变了,由老师变成学生了。我觉得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才是真实的课堂。我看了我们的课堂以后,特别是老师站着讲课,学生坐在那里,老师讲老师的课,学生做自己的事。我把这样的课堂比作领导开会,领导坐在主席台上,服务员倒好茶水,秘书把稿件放好,音响师调好话筒,主持人说:“同志们请坐好,现在开会。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作重要讲话。”这时整个会场听主持人的(他让我们鼓掌我们就鼓掌,他让我们关闭手机我们就关闭)。不一会儿你就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有的开始说话了,有的开始方便了,有的开始打电话订饭了,有的开溜了。台上的主持人有点坐不住了,用尽了种种招数,什么录像、点名、通报等等都没有什么效果。我们越来越发现,开会成为了大小官员的负担,都知道是负担,但是都不能改变。你能说开会没有一点用处吗?你能说开会完全是形式吗?你能说开会时领导的讲话稿写得不好吗?都不是,我总觉得与自己的切身利益联系得不紧密,或者干脆说没有多大用处。会议还好,没有用处无非耽搁你们一些工夫,如果是课堂那可就不是耽搁工夫了,那要耽搁孩子一生的。对于课堂我要求的不是那么死板,大家可以灵活掌握,主要是强调以下几点:
一是把教学变成学教。问题不大吧,你看,字都没变,只不过是调换了一下位置。有难度吗?应该是没有。也就是说,你过去是拿着书本走进课堂干什么来了?教学生来了。你特别清楚一名老师的职责,备好课,上好课,教好学生。然而你都做到了吗?没有;你说你没有用心吗?心都快操碎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有一个拉车和推车的比喻。教学以我的理解就是教和学,就是老师教、学生学,老师只管教自己的,学生是否学自己的那就很难说了。还有的老师早已设定了进度,这一学年我讲多少、这一学期我讲多少、这一节课我讲多少,他从来不知道这一学年学生学多少、这一学期学生学多少、这一节课学生学多少。一直以来,教跑在前面,学生落在后面,能追上的就追、追不上的就算了。龟兔赛跑,兔子跑得太快了,它就是随意找个树凉睡一觉,心想,它还是追不上我的;乌龟实在追不上了,干脆想我不如也睡上一觉,于是倒头呼呼大睡起来。所以我经常说,教学是老师按照计划讲自己的课,讲他自己感兴趣的课,学生唯一的选择就是学生的“学”服从老师的“教”。你可以算一算,这么多年来我们葬送了多少学生的前途。最可怕的是一些名校老师的观念,课堂是场战斗,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为了保住几个升学指标,或者说得明白一些是能够保住几个考上清华、北大的,而不惜牺牲众多学生一生的前途。你是否听说过那些名校公布多少没考上的人数,他们后来都去干什么去了。我认为教育千万不能功利,千万不能只为了几个人,而要为了所有的孩子。
学教就不同,主体变了,教是围绕着学。老师的备课、教学活动、教学计划都围绕学展开。因材施教,因情况施教,因发展变化施教。学生主动了,不再是“要我学”,而成了“我要学”。教育教学一下子成动态的了。
二是把依赖变成主动。我们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主动行动的能力,让他们渐渐摆脱依赖老师、学校的心理。如果学生仍然依赖我们,那只能证明现有教育教学手段依然流于形式化、教条化。
三是把装样变成真实。我最怕装样子,我在《做整个的校长》里说过要把功夫用在平时。我最怕打扫卫生为了让领导看、上课为了让领导看、考试为了让领导看,就连晚上睡觉也为了让领导看,姿势摆得端端正正的,舒服吗?不舒服,太难受了。更可怕的是人死了也要让领导看,尸体上挂满奖章,戴上帽子,死也得一本正经的死,可是到了最后一道工序就不怕你了,火葬都得烧成灰,不管怎么烧,结果都是灰。我经常为领导叫苦,累不累?自找的,你不管不就是了;我也经常为装样子的人叫苦,容易吗?实在不容易,不过也活该!我经常转课堂,有老师问我讲得怎样?我说我要看学生的状态怎样,我就知道他的课怎样。我写过一篇《“八真”课堂》就是:“真课堂,真状态,真讨论,真放手,真质疑,真课改,真自信,真鼓励。”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大国人文》栏目组编导贺江女士用了一个“真”字标题《怎一个“真”字了得——祝卫国和他推行的生态教育》,一开始就直奔“真学校!真教师!真学生!”的主题。于此,真!显得弥足珍贵。
鲜花在前面,我们在路上,一路前行,必将踏进幸福的人生花园。
用才是最好的教育
大家齐唱一首歌《幸福在哪里》,我再讲幸福在哪里。
我来告诉大家幸福在哪里。幸福在人生的追求里,年轻人搞对象,“我终于将那个女孩追到手了”,幸福吗?“太幸福了,还幸运!”幸福在事业的发展里,女朋友追到手了,咱不能每天什么也不干,天天坐在床上欣赏吧,小两口要过日子,买房子、买汽车,这还不算,男人在建筑行业还要拿到鲁班奖,女的在教师队伍里是佼佼者,是改革能手,这些都是通过努力得来的,所以他们觉得很幸福。幸福在创造的火花里,人类的智慧在于他们知道与时俱进,所以社会才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才给人类带来了更多幸福的体会。
就一个人来说,他的身体由许许多多器官组成。我且不论这些器官它们各自的作用有多大,我是说他们都没有闲着也不能闲着。如果跑步时,胳膊所起的作用不大,我们把它捆起来;写作时也没有人用脚思考,我们也把它捆起来;说话时除了用嘴之外其他部位几乎都不起作用,那就都捆起来,但是如果把眼睛蒙上,那么你就几乎是在说瞎话了(睁着眼不看对方表情那叫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要调动整个的身心做事,对于一所学校来说,要做整个的学生、整个的老师、整个的校长、整个的学校。
用心做整个的校长
当校长的最怕你不用脑,最怕你不动脑,最怕你不主动,也最怕你机械地理解领导的意图。其实,任何当领导的都怕他的手下一味地迎合他而不是开创性地工作。当然,任何一位校长也不希望他的老师死死板板地等待校长的要求。我想,我们都一样,都希望自己的老师不仅很好地执行了学校的教学常规要求,更希望看到他们创造性地发挥各自的能力。我在《做整个的校长》里提到:“潜下心来教学;俯下身子做事;静下心来研究;埋下头来读书。”
我觉得一个老师的真实来自于校长的真实;学生的真实来自于老师的真实,真学生,主动求知并能够愉快地生活。有了这些真实,学校才是真实的学校。
如果我把学校比作一辆汽车,校长好比发动机,至于老师和同学比作什么,我把这个想象交给你们。大家知道,发动机也不一样,也不是每台发动机都那么优秀。假如你是一台高品质的发动机,那么就会牵引这辆汽车高效运转;假如你是一台普通发动机,那么这辆汽车跑起来就不会随心所欲;假如你是一台有毛病的发动机的话,那么谁驾驶这辆汽车都会担心,如果这辆车开到大街上,知情的人都会捏一把汗的,然而驾驶的人和这辆汽车并不清楚到底有多危险。我们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发动机,也决定着这所学校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这就是为什么老百姓挖空心思也要为孩子选一所好学校的原因。当然,有人会提出一些常规的问题,比如说,发动机与汽车部件的关系,他们甚至还会提出把一台高品质的发动机安装在很一般的外壳上,以及一些不配套的从动系统上。尽管这一切不是发动机本身可以改变的,但是假如这些系统都配套的话,那么发动机的作用显而易见。如果发动机不知疲倦地工作,那么这辆汽车也会发挥它最好的效率。我于1996年取得驾驶证,到2007年为止都一直装着驾驶证骑自行车。尽管没汽车,但我每天看看证件心里也觉得很满足。2007年以后我任市教育局装备站站长,配了车,到现在一直开着。我有一个感觉,开车最好的感觉不是车有多好,而是不管开多快,说停就能停下来,说停到什么位置就能够停到什么位置,这叫随心所欲,如果这四个字再升华又成了四个字——“人车合一”。如果你是校长能否人校合一,是老师能否师生合一,是学生能否生生合一。都合一了,还有办不好的事吗?还会出事吗?你还能不幸福吗?
2010年12月,我任十中校长。这是一所没什么名气的学校,恐怕在座的听说过这所学校的不多。可能在你们的印象当中,只记得那几所规模大一些的学校。我发现穷学校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穷的原因是不勤快。症状是,冬天怕冷、夏天怕热,都躲到屋里不肯出来。所有懒人有一个共同的懒特点,都不愿意活动,这是说身体方面的;另外,还有一个是头脑方面的,不愿意动脑。你看吧,他们上课就像陶行知形容的那样,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每天上课铃声一响,老师无精打采地往讲台上一站,学生个个愁眉苦脸、少气无力、稀稀拉拉地喊道:“老、老——师、师——好、好。”这就开始上课了,这上课比老和尚念佛经都枯燥。干脆,大胆的学生也就不给老师面子了,睡吧!不一会儿就进入梦乡了。我看课堂死一块活一块的。懒人多的地方有三懒,老师懒、学生懒、工人懒。说工人懒,你看教室里四个灯泡坏了三个保证能凑合;电扇不转了保证不怕热;厕所冲水阀漏水保证没人管;门窗都快掉下来了保证能原样不动;电器上的螺丝松了保证没人拧;门口的人进进出出的,保安钻进屋里保证不管;花草不长茅草横生。平时都这样,一放假保证没人来,放一百天也一百天没人来。
第二个穷的原因是不主动。不主动就是你让我干多少我就干多少,你不指名道姓叫我,我是不干的;还有的是中国传统特色的思维,我要干就得让领导看到,如果领导不知道那我就等于白干了,于是装样子的多了。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学校里无论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要我亲自发现,否则大家都视而不见。不主动表现在教学上就是老师不主动、学生不主动。老师有什么教什么,知道什么就教什么,会多少就教多少,一切听凭我有多少而不是我还有多少,我有多大潜力,我能创造多少。于是我发现,图书馆是摆设、实验室是摆设,以及所有的除了教室之外的地方统统是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