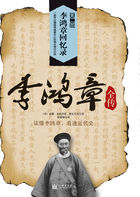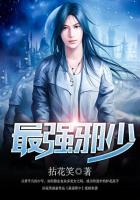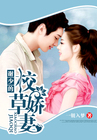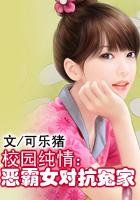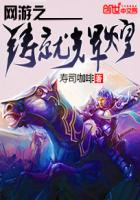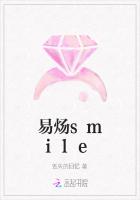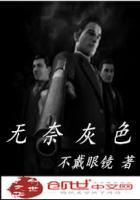“苏东剧变”给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在骇然之余,思想界形成了几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苏联和东欧各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和阶级斗争学说才导致了今日的政权丧失。这一思潮当然对吴敬琏等改革派人士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压力。
1990年的春天,吴敬琏偕周南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回国时,途经刚刚合并的联邦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变幻让他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
吴敬琏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最深层的原因,乃是由于体制的缺陷和建立在这种体制基础上的政策失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有些国家企图对这种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建立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由于目标不明或方法不对,也没有能取得成功。这样,经济情况愈来愈糟,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失去了信心。他最终的结论是:中国只有进行改革开放,才能确保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就在吴敬琏归国后不久的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在座。吴敬琏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
与前一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
这时,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 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改成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其间,还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的,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市场取向改革的一边,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应当恢复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提法。而在论战的对方,除了许毅、袁木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当过《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有林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一时间,双方互不相让。86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桥也谈及了他对“苏东剧变”的看法,他写道:“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苏东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这封信在起草过程中得到吴敬琏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我写的原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
为了呼应薛暮桥,吴敬琏也继续顽强地反批评。在1990年11月,他写出《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一文,对未来10年的改革进行了战略性的思考。
针对困难重重的局面,吴敬琏把当时各种政治力量提出的解决之道概括为以下三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实行行政性的重新集中化,废止前几年施行的行政性分权体制,如“财政大包干”等等,取消价格双轨制,加强中央对稀缺资源的集中控制,把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重要产品的生产和主要投资置于指令性计划的控制之下,用行政性手段进行资源的再配置,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换而言之,就是退回到中央集权的计划模式。他判断说,“这种办法如果能够实现,是能够实现短时期的经济稳定的”。但是,中国的变化将从此非常缓慢,“不能指望依靠它来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第二种方案,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尽快取消“双重体制”,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系初步地建立起来,在强化国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控制的同时,充分运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克服现有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转的种种问题。
第三种方案,大体保持现有的计划-市场双重体制以及“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信贷大包干”、部门承包和企业承包等制度,只在两个方面做一些改变,一是适当加强中央行政当局和计划机关的权力,增加指令性计划的比重,二是对某些不太合理的价格作某些调整,对承包基数和方法作修订和改进。
吴敬琏认为,合意的是第二种方案,不过他认为被采纳的概率很低,他写到,“虽然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坚信这是中国经济摆脱困境、走向繁荣的道路,但是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和10年来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这种想法恐怕很难为人们所接受”。所以,他几乎无奈地认为,第三种方法——“从政治上说也许是较为可取的。但是中国经济现实存在的问题则很难由此得到解决。如果继续保持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则中期经济不可能有大的起色,而如果采取放松货币控制的办法刺激经济回升,又很容易出现新的一轮扩张——膨胀——紧缩——萧条的波动。”
在文章的最后,他颇带期望地写道,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真正成功,“出路在于推进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较快地建立有宏观调节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后的发展中,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专家和领导人认识这一点,因而出现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写作此文时的吴敬琏并没有料想到,他所期盼的“在今后会出现的那个领导人”居然不久就出现了。两年多后,在他给出的三种方案中,中央政府最终采纳的居然不是折中的第三种,而是最具市场化特征的第二种。
这些当然是后话。至少从1990年前后的公开舆论看来,吴敬琏和薛暮桥等人仍然是孤独的。
就在勤政殿座谈会开后的4个月,199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刊发文章,标题是《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完全实行市场经济》,其核心观点直奔市场取向派而去。1991年4月,《当代思潮》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7月,《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姓“资”》,说“一切不愿意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在改革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问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偏离改革的方向”。北京一家报纸则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提出“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社’姓‘资’,更有甚者,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在潜行”。
1990年年底的一天,吴敬琏的老朋友乌家培给他打来电话。在寒暄数语后,乌小心翼翼地询问说,“你知道最近外面给你起了一个什么绰号吗?”吴敬琏茫然地说,“不知道。”乌说,“计委那边有人说,目前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有计划’(指有林),一个是‘吴市场’,还有一个是‘杨承包’(指杨培新)。”
也就是从这时起,“吴市场”这个绰号不胫而走。日后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及,“‘吴市场’对我完全不是美称,当时是很厉害的贬义:‘和中央不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