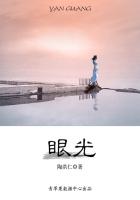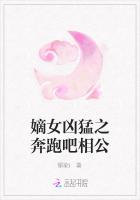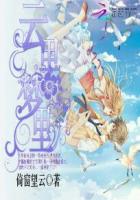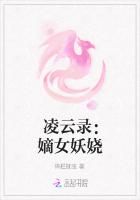如此,人们在强权面前的潜台词就变成: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正好是你要的那个东西,我是你的逻辑,你的立场。这下你没有什么可说了吧。如果犯错误,那是你的错误、你的不幸和无力,与我无关。你的错误由你来承担,我的错误也由你来承担。因为我就是你。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反而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他不是失败者,而成了得胜者。在这种貌似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人眼睁睁地从任何责任感中逃脱了。
某种情况很像是在王小波的小说里发生的。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里的王二,作为在豆腐厂工作的工人,他需要在输送豆浆的低空管道上行走,甚至这成了他的一桩爱好,很难说这仅仅是因为工作的需要。革委会主任老鲁不停地要捉拿他,他必须不断逃离。读者或许产生这样的印象,老鲁想要捉拿他的外在现实,变成了他的内在要求,这样他正好可以捉弄老鲁,以对方的逻辑,借此戏弄对方。他东躲西藏却又抛头露面,他在空中飞来飞去却又不断落地。
有一次他被老鲁抓住了衣领,但那个领子是白纸画的,轻轻一挣脱就被撕成了两半,他本人就如断了尾巴的壁虎一样逃走了。还有一次他真的被老鲁抓住了,直不楞登地倒在地上看似气绝身亡。老鲁被吓得赶紧把他往医院送,送出厂门他就活蹦乱跳了。气得老鲁说,下次王二再没了气,不送医院,直接送火葬场。
在小说里幽默一把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在现实中,重复他人的逻辑和错误,并不意味着找到自己新的起点,而恰恰会掩埋自己原来的立场,歪曲自己的感情。让人性停留在恶作剧的水平之上,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进来,富有意义的东西仍然被排除在外。长此以往,策略也会长成人的面具,戴在脸上拿不下来。以一种空洞去对付另一种空洞,一种虚无去对付另一种虚无,一种同样是掩饰来对付原来的掩饰,这当然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只要顺势就行。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我让你没法找碴儿的做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伟大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实际上,我可能认为那是一个野蛮国家,对此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英雄”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憎恨把人们的人性拉向比较低矮的去处。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艺术的唱片,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位,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到正在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并因为自己拥有这些伪装的技巧而感到暗自满意。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统治者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而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人们摇身一变,披上了“新人”的外衣。他们表现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并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米沃什认为,伦理凯特曼,是一种最为强劲的凯特曼,包括能够做到对原先的朋友铁面无私,告发周围的人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就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无从打听。结果是人们患了各种精神分裂症,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一个人与他自己相分离,与他自己之间隔着一条大河,他弄不清楚在他自己身上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重要的;弄不清什么是该喜欢的,什么是该抛弃的。事情原有的界桩被一再移动,他日益变得模糊含混。
对一些人来说,他们一开始也许并不是故意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因为拥有某个不谨慎的开头,继而步步迈向谎言的深渊,越走越深,难以自拔。如果说最初还有良知的愧疚,知道自己的良心在什么地方,渐渐地,他变得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因为他本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模模糊糊地认为能够蒙混过关就是真相本身。即使他原来是一个普通人,结果照样也可以挑战社会和他人:打着真与善的旗号,兜售他本人的假和恶,与他的大环境处于互为辉映的“镜像关系”当中。
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人们离事情的本源久矣,不知羞耻成了新的道德观。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因此该书既是与他留在波兰的朋友之间的对话,也是与他自身的对话。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今天特别匮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也应该包括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以自身的道德努力,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复原。一个人起码要坚守住自己,不能让自己成为一块仅仅是遭受损失的大陆。
波兰历史学家亚当·米奇尼克(1946—),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想起了诗人米沃什的诗句。1982年,米奇尼克写道:“当你独自站立,眼睛遭到催泪瓦斯的刺激,警察在你面前晃动着手枪——在这漆黑的、没有星光的夜晚,多亏了你最爱的诗人,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雪崩的形成,有赖于滚落的石子翻个身’(切·米沃什)。于是,你想要成为那块扭转事件方向的石子。”
四
书中还有四个令人信服的人物故事,应该都是有现实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甚至是一些思想气质十分边缘的人,如何逐步进入了“历史”的大门。在一个宏大背景之下,他又提供了具体的个案。其中“阿尔法,道德家”是最有深度的一个。阿尔法这个人本身追求完美、纯洁,力求无懈可击,这使得他的选择带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这是一位作家,在战争期间也会以作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创办了地下文学刊物,写作有关“受难”、“忠诚”主题的小说,表达了与纳粹决一死战的精神状态,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来说,祖国和荣誉高于一切。然而,还存在着个人信念之外,比个人信念更为强大的力量,那就是“现实”。实际情况是,地下抵抗带来了重大牺牲,同时更多的人在集中营里被枪决。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命运时,仅仅为个人拥有的“忠诚”概念便显得远远不够。
1944年的华沙起义,将这个问题推至极端。这是由远在伦敦的波兰“地下国家”发动的。其时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易北河对岸,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的马匹在河边喝水和洗澡。情形的复杂性在于,波兰人对俄国人同样忧心忡忡,深知其吞并或瓜分波兰的野心不死。因此,对于指导起义的流亡政府来说,便期盼能在红军到来之前,有一个已经运转的波兰政府,这样才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自己手里。这个思路有其道理,然而现实却不允许。
米沃什形容为“这是一只苍蝇反抗两个巨人的搏斗”,其中一个巨人(俄)比另一个巨人(德)更有耐心,等待着苍蝇被一个巨人杀死之后它才出场,始终按兵不动。结果是,两个月内华沙上空浓烟滚滚,手中武器为手枪、手榴弹、燃烧瓶的人们,完全不能抵挡来自德军的轰炸机、坦克和重炮,二十万人痛苦地死于残酷的巷战,华沙变成一片废墟。幸存者逃进了森林,如果仍然忠诚于他的波兰祖国,而不是屈服于苏联红军,会被当作“起义的法西斯”。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忠诚”,便显得无效、愚忠、狂热,甚至可笑。
米沃什回忆了他本人与这位道德小说家,一道迷失在华沙起义后的废墟瓦砾中的情景,他们“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幻想中的月球景观。这里一片沉寂”。一个意想不到的小木板出现了。它吊在一个金属栅栏上,上面用红色的漆写道:“兹比舍克中尉的受难之路。”谁是这位兹比舍克中尉?有谁知道他到底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所携带的是什么样的任务?他是谁的儿子?或许是一个邮政官员的儿子?没有人知道这些了。那块木板上的字,就像是“从一个被毁弃的大地抛向天空的一声呐喊”。一对朋友同样承受了这个来自死亡边缘孤独声音的巨大冲击。
那些走向新秩序新信仰的人,便怀着这样无边的绝望。而这也是米沃什本人曾经的思想道路:“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说话时,他几乎是带着疼痛喊出来的。
那么米沃什从什么地方开始走向“歧路”?他与朋友的分歧出现在何处呢?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通过他的叙述完全可以找到线索。这位被他化名为阿尔法的朋友拥有一种天生的抽象性,对概念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具体人的兴趣,他的小说中具体的人及其生活背景,常常被概念所扭曲,变成服从概念的需要。此类需要也是建立权威的需要。而对于米沃什来说,具体的、活生生的、有名有姓的人,比任何抽象的概念(方向)要重要得多。
阿尔法写出了他的新小说,关于纳粹期间的华沙生活。米沃什这样评论道:“阿尔法在被蹂躏的城市中给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当时那可是‘热门的话题’,却让我们时常有一种奇怪而不自在的感觉。他竟然这么快就利用这些题材做文章,而且处理得如此顺畅。成千上万的人在我们身边受尽折磨致死,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惨的戏剧场面,这样做,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成体统。”这里指的是,对那些身体还未凉透的人,要有一种敬畏和距离,而不是马上给他们涂上胭脂。宁愿站在沉默一边,也不要站在喧哗一边。宁愿失语,也不要背叛心中悲哀肃穆的感觉,更不要马上去学会强权者的语言和腔调。
书中“波罗的海”这一章,他发出了一生中少有的尖锐批评。1944年,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的政策,使得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劫掠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这一切。东方和西方的舆论没有关注这些。
他尤其提到自己手中拿着的一封信,它来自原先生活在波罗的海的一个家庭,一家三口,母亲与两个女儿,于1949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信中以干巴巴的简短语言叙述了她们在集体农庄工作的情形,而信的每一行最后一个字母都很粗,将它们连在一起看,就出现了“永恒的奴隶”这个字样。这是被抹杀中一声悲苦的叫喊。米沃什从中想到了“还会有多少人想写信却没有写出来?还有多少可能会写这种信的人,因饥饿和过度劳累死于冷酷的北极地区,死时仍然在不断重复这句令人绝望的话‘永恒的奴隶’?”
炫耀的强权与被沉埋的人们在诗人身上进行拉锯,就像曾经不同的力量在争夺和分割他的家乡、他的祖国。他自己经历的下面这个故事,同样体现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个夜晚,作为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在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
米沃什决定停下来了,他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有人将“人”和“历史”对立起来,经过迟疑斗争,米沃什最终选择了“人”:具体的、生活在某处的人,有着熟悉亲切的面庞。他决定背负来自出身地的无边苦难,承担那些永远沉埋地下的人的痛苦。他选择站在了失败者一边:“我是站在未来的胜利还是被战胜的人一边,我的将来是赢还是输,全都无所谓。我只知道,如果我的朋友将尝到甜美的胜利果实,如果地球经过长达数百年计划经营而得到改造,对能活到那个时候的人来说将是极大的悲哀。”这几句话表明,米沃什同样拥有奥威尔那样的预言能力。这种能力并不神秘,是一个艺术家对人类事务的关心所拥有的穿透性目光。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说得对。
实际上,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同时显出两副面孔:一方面是华美的和欢快的;另一方面是被掩埋,是痛苦的喊叫。这是米沃什写在1943年的一首著名的诗《菲奥里广场》,其中一边是在美好欢笑中度周末的人们,不远处的另一边便是犹太区着火的房屋、被风吹散的黑色碎片。前者对于后者全然没有感觉。然而,暴力正是在人们的忽视中开始变得流行,悲剧在人们的轻率中一件接着一件发生。
一个晴朗的春夜
在华沙按狂欢的曲调
旋转木马旁的我
想起了康波·代·菲奥里
兴高采烈的旋律淹没了
犹太区屋墙传来的炮弹齐发声
双双对对高飞
在无云的天空
有时从火堆吹来的风
把黑色风筝吹过去
旋转木马的骑者
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
那同一阵热风
还吹开了姑娘们的裙
人们开怀大笑
在那美丽的华沙的星期天
(绿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