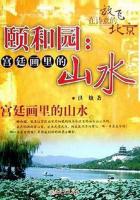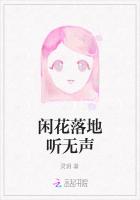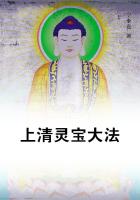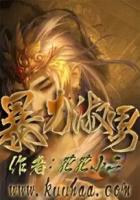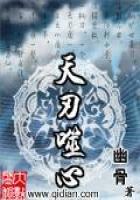其次,重刊各译本应明确注明所据版本,不能含糊其词。《胡适译短篇小说》的“出版说明”中云:“第一集到一九四〇年已经印行了二十一版;第二集也于第二年便再版了一次。”是否此次重刊所据为第二十一版的《短篇小说》和第二版《短篇小说》第二集?如果找不到初版本,尽可老实注明版次,便于研究者使用,因各版内容可能并不一样。比如《域外小说集》,此次重刊显然依据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的合刊本,而不是一九〇九年东京出版的初版本。初版本与合刊本的《著者事略》有很大差别,若据此次重刊本的《著者事略》来论证一九〇九年周氏兄弟的文艺思想,那可是要闹笑话的。这并非绝不可能,重刊本给人的印象是依据初版本重印的,而初版本一般专家学者都不容易见到。
再次,重刊本最好能附录一点研究资料(如《域外小说集》重刊本所为),尤其是当年读者的反应和专家的批评,这样可以增加重刊本的学术价值。编者写后记或出版说明也是一种扩大读者视野的好办法。不过,这就要求编者有一定的学术修养,才能评判公允论述精当。《欧美名家短篇小说》的“后记”中有这么一段话:“译者将这些译作按国家编为上、中、下三卷,又于每篇作品前,写下原著者小传。小传用文言文,简约扼要,足见作者对外国文学研究的渊博和郑重。”依我看来,周瘦鹃显然是依据英文本的短篇小说选集选译的,而英文本大概原来就有作者小传和照片,要不周瘦鹃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一年)找到那么齐全详尽而且体例一致的传记材料,更不要说作什么“渊博”的研究。也就是说,周瘦鹃所译每篇小说前的作者小传,是译的而不是著的。这一点跟周氏兄弟译《域外小说集》写《著者事略》和胡适译《短篇小说》写“前言”不同,后两者于其中确实可见译者的文艺观点和鉴赏能力,前者则只能说明译者工作态度认真,“用心颇为恳挚”(借用鲁迅、周作人所拟评语)。
(《域外小说集》,会稽周氏兄弟旧译,巴金、汝龙等新译,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第一版,平装本2.35元,精装本3.35元;《天方夜谭》,奚若译,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平装本4.00元,精装本5.00元;《胡适译短篇小说》,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七月第一版,平装本1.15元,精装本2.15元;《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周瘦鹃译,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第一版,平装本3.25元,精装本4.2元)
(一九八七年第十二期《读书》)
温和的意义:漫谈《知堂书话》
李书磊
《知堂书话》是一部谈书的书。钟叔河先生把周作人散见的书话辑为一书由岳麓书社出版,真是便利了爱书的人。毕竟相隔几十年了,读书环境有很大变化,周作人所谈的那些书很多我都没有读过。但好在周作人的书话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好摘引,大段大段地,很下得去手。这大规模的摘引使我领略了那些书的精华。在“伪创造”的浮躁之风盛行的今天,看到周作人几十年前这种心平气和的摘引,让人很愉快。这种摘引的功夫,已不仅仅是一种耐心,简直就是一种雅量了。
但周作人的妙处并不仅仅在摘引,他那许多似乎是随手写下的评点,读来都让人拍案叫绝。然而这本书最吸引我的还不是这些评点本身,而是这些评点所流露的、所凭借的文化态度。那是一种冷静的、宽容的温和态度。《知堂书话》谈及的书有几百部,古今中外,其中甚至不乏与周作人所坚持的新文化精神大相径庭的书,但他都能较为客观地说出它的好处来。如《颜氏家训》,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许多人看来是一部典型的儒家旧典,应该大加挞伐的,但周作人偏就能从中看出这部书“兼好法师之可喜”,看出其“人情味之所在”,从而不带偏见地加以赞扬。周作人在文化上无疑是坚定地站在“五四”新文化阵营一边的,他对中国传统中那种反人道内容是坚决否定和反对的,这从《知堂书话》中也可以看得出来,如他在谈到郁达夫的《沉沦》和霭理斯的《性的心理》时所表现的性开放态度、谈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时所提倡的现代教育观念就是证明。但他的特点是进步而不激进,坚持新的而不囿于新的。他没有把新文化推到一种唯一的、极端的地位,没有把它神圣化。在经过一九八五、一九八六年令人激动的文化论争之后,重新审视周作人这种文化态度,我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深长意味。
在中国文化的改造上,周作人是属于温和派的,这一派也是非主流派,它的代表人物还有胡适等人;主流派是激进派,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激进派后来占了上风,赢得了青年和社会的支持,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面貌都产生了极为重大也极为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复杂性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我们,这使得《知堂书话》这部重编的旧作仍具有尖锐的思想刺激性。
我一直不太喜欢周作人。这倒不是因为他担任过伪职,而正是因为他这种温和态度。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直受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激进态度的熏陶,对鲁迅的精神有一种自然的共鸣;再加上我们身处在中国传统旧文化的直接压迫之下,长期痛苦的切肤之感激起了一种本能的、暴烈的反抗情绪,所以我们总是意气难平,总是不能平心静气,一提起这个话题就激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喜欢温和?这也是我在前一阵的文化论争中一直坚持对旧文化全盘否定、彻底抛弃论的原因。但最近我开始重新反省这一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占了上风,但后来的社会结果却是中国旧文化和旧传统不断得到强化和泛滥,一步步地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我直到今天仍然反对那种把“文革”中所谓的“破四旧”和“五四”时代的破旧等同起来的无知而可鄙的论调,但我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态度与“文化大革命”有一种因果关系。尽管这种因果之间有许多中间环节,如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接受等等,但这种因果链还是可见的。这是一个新文化的先驱者始料不及、与他们意愿相反的大悲剧。事实上我们不能不承认用激进的方式来改造旧文化是失败的。或许新文化的激进方式本身就是违背新文化而适合旧文化的。我发现旧文化最可怕的也许不是它的文化内容,而是它唯一的、专制的存在方式和它的排他性,用新文化的专制去代替旧文化的专制,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态度的核心;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专制方式本身就是对新文化内容的否定和背叛。所以想要达到新文化的专制就必然带来旧文化的专制,问题就出在专制的企图上。专制形式是属于旧文化的,逻辑和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就像所谓“红色恐怖”不可能真正消灭“白色恐怖”、善的人们以恶抗恶不可能真正消灭恶一样。所以这就要求反抗者有一种超人的人格力量:他受到野蛮的压迫,但他却必须用文明的方式去反抗这压迫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正是出于对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的失败的追究,我重新估价新文化运动中这被长期忽视的另外一派:温和主义。温和主义也是一种宽容主义,这在今天显示了一种新的光采和魅力。也许只有温和主义才能给新文化带来最后胜利。这就是我阅读《知堂书话》的心理契机。我也向青年同道们建议读一读这本书,读一读,想一想,受点启发。不加反省地坚持原来偏激的激进态度是痛快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太痛快的东西都很可疑;接近自己精神上一直抗拒的东西是痛苦的,但这痛苦却是我们不能逃避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由激进转向温和,事情没那么便当,我们也没那么轻率,但多往几个不同的角度思考一下,多推敲、反省一下是决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最后我还要声明这种反省决不是对国粹主义的认同。文化改造方式的改善和文化立场的转变不是一回事。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即使真的错了也不减弱其伟大的道德力量。我一直认为国粹主义是一种愚昧,新旧国粹派的存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耻辱。我今天仍这么看。
(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四日《光明日报》)
温和的别一种意义:也谈《知堂书话》
赵京华
《知堂书话》的出版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证实了五十年前的周作人的这些文字的价值和魅力。但我不赞同李书磊所认同的那一种“价值和魅力”即“温和主义也是一种宽容主义”的文化态度(见本刊第七期《温和的意义:漫谈〈知堂书话〉》一文)。
《知堂书话》,包括周作人二三十年代绝大部分的小品散文,的确表现出一种“冷静的、宽容的温和态度”,也借此使周作人的文化批判与艺术创作在新文坛上独领一代风骚。但我读周作人,尤其是读了五四时期“浮躁凌厉”的周作人,再读二三十年代平和冲淡、儒雅“温和”的周作人,总有一种儿时读《水浒》后半,梁山泊大业江河日下之感。究其原因,在于周作人这种温和宽容主义文化态度是包容在他所追求的东方古典式的平和、冲淡、闲适的审美情趣之中的,对于接受了现代精神洗礼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这种回向传统境界的追求并非其初衷,周作人后来的走向温和与闲适就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作为反封建的战士,在批判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时,得出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民族失败主义的结论。他感到“五四”以来我们无论怎样地批判旧文化、旧人格,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保存国粹正可不必,提倡欧化也是空虚”,对于中国的改革失去了“九层”的信心。因此,他要冷静下来,找一点温和的东西来读,并写一些温和的东西给寂寞如他自己那样的一些文化人去读。以“温和”到几乎是冷眼旁观的态度去“察明同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痛苦”,他明明知道是“虚空”,却还要“追迹”下去,不过是作为一种“有趣味的消遣”(《看云集·伟大的捕风》),以抚慰那颗曾经战斗拼搏过的寂寞的灵魂而已。这之中是不是有种中国知识分子身处历史重负和现实苦难,包括东西方文化冲突之中所产生的人格分裂或无可奈何的心态?是不是有那么一些“苦味”,一些“悲凉”?甚而至于文化思想上的退守姿态?
作为一种文化态度,“温和主义”本来可以导向两种不同的文化立场。或者走向理智主义,与急功近利的现实目的拉开距离,以科学理性为基本价值标准在更高的历史哲学层面上评断古今文化,渐进地累积起中国新文化的坚实理论基础;或者走向保守主义,在难以超越的强大的改革阻力面前,用“温和主义”的“宽容”姿态一步步向后退守,借此掩饰文化人思想超前而又无力把超前的思想诉诸社会改革实践的“尴尬局面”。“五四”以来文化上的“温和派”后来大都走向保守主义,在不自觉地回归传统、拥抱旧文明中,找到了慰藉心灵的温情脉脉的精神家园。只可惜这是一片破败的旧家园,它有着无限“精炼的颓废”!自然和谐、中庸平正、宁静飘逸、闲适冲淡,满含着身栖漫长专制时代的东方人欲求摆脱无尽的世间苦难而不得所产生的虚幻、萎靡、苦闷的深层心理情绪。这是一个可怕的令人颤栗的美丽境界,走进此境界往往是以丧失生命搏击的意志力、个体人格独立价值以及主体的自觉理性自由表达为沉重代价。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以及最悲惨的知堂老人莫不如此。
因此,我理解“五四”以来的温和派,他们毕竟是新旧文化历史过渡期的一代知识分子,饱受旧文明的滋养,难于超越情感血脉中旧文化的遗传因子,身处传统崩溃的现代社会,他们的心灵是倍受煎熬的!但我不能认同于他们的“温和”,相反地,对“五四”以来的“激进派”则始终感到一种真正心灵的共鸣与契合。所谓“激进”可以有两种内涵不同的形态。一种是“理性的激进”:如鲁迅等那样理智地对待历史、历史地对待文化,把批判的理性包蕴在充满生命热力的挑战姿态中,并以独立的不妥协的人格精神力量向旧有的、衰亡的文化进行批判,这是一种认定了历史进化必然性,经过了理性洗礼的“激进”。另一种是“疯狂的激进”:处于心理和生理的病态状况之中,没有主体意志,没有历史目标,只是盲目地毁坏一切,而且是以最低级、最野蛮的形式进行毁坏!如果硬要把五四文化革命和五十年后的“文革”拉扯到一起的话,我只能说,“五四”的“激进”是理性的激进,而“文革”的“激进”则是疯狂的激进,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联系的。
最后要声明的是,作为审美层面上的艺术品格,《知堂书话》的温和与宽容是无可挑剔的。但是,作为一种旨在改革现实的文化立场与态度,无论温和主义还是宽容主义都无助于文化改革与重建的成功。青年同道们读周作人时,既要有一种雅量,又要有一点审视的眼光。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光明日报》)
《知堂书话》和周作人的文化态度
黎澍
【《光明日报》编者按】
本刊第七期和第十期发表的《温和的意义:谈〈知堂书话〉》和《温和的别一种意义:也谈〈知堂书话〉》两文,引起了读书界的反响,日前本刊编辑李春林拜访著名历史学家黎澍,请他谈《知堂书话》和周作人的文化态度,下面是黎澍先生的谈话记录。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本刊欢迎读者继续来稿。
《知堂书话》里的许多文章以前都读过,现在再加翻阅,有一些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