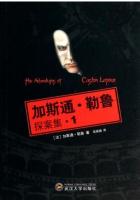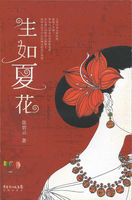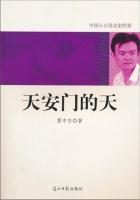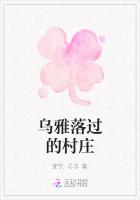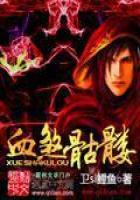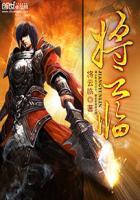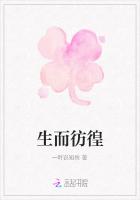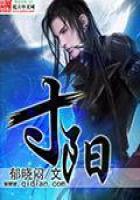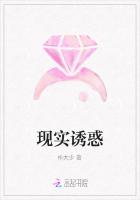坐了一会,童贯问道:“游大人,贵地可有什么好宝物?”游酢听了,怕他来和州搜刮老百姓,笑着回答:“苏、杭是人间的天堂,江宁是古都,那些地方才有许多的宝物。这和州,童大人谅也知道多少分量。”童贯是个极心细的人,见游酢这么说,想了想,说道:“游大人说得也在理。不过,偌大的和州该不会一点宝物都没有吧。”游酢又笑了笑道:“我一向忙于政务,不曾留意过。如果童大人听说或者发现了什么,尽管吩咐,在下遵旨意照办就是。”童贯明白游酢话的弦外之音,说道:“童某不过顺便问问而已,哪里敢耽误游大人的政务。我这就回杭州去。”游酢忙起身说道:“童大人别误会,千万不能就这么走。俗话说‘客来主不顾,非礼也’,你我何况是在京城就相识的故交,又是同代人,童大人要是看得起游某,就留下,中午咱们俩好好喝两杯。”童贯应道:“既然游大人如此诚意,盛情,那么童某就再陪游大人坐一坐。”
这天中午,游酢到“太白楼”热情地款待了童贯一餐。童贯身体极棒,午后休息了一回,便起程回杭州。
送走了童贯,游酢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日,游酢同吕氏商量道:“老三今年已经十八岁,如果有适合的人家闺女给他成个家,出些钱让他做点生意就是。”吕氏说:“老爷说得也是,只是不知找什么样人家好。是老家的?还是这里的?”
却说和州城内有一位绅士乃杜默的后代杜善,家里资产百万,开着好几家店铺。他有一男一女,儿子杜进与游拂玩得极好,亲如兄弟;其女儿杜丽,长得端庄秀丽,人也天资聪慧,不但女红无所不能,而且能够通晓诗书,年方二八,按照当地习俗已经到了论嫁的年龄。杜善看上了游拂,觉得这孩子忠厚诚实,况且其父亲游酢乃朝廷命官、当今和州的老爷,便私下托管家前来提亲。
游酢同吕氏热情地接待管家。管家说明了来意之后,游酢回答道:“孩子的婚事,虽然自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我们夫妇还得征求一下孩子本人的意思。过一两天再说吧。”管家走后,吕氏与游酢商量道:“现在杜财主找上门,可谓真是巧合。只是不知老三有没有想头。”游酢答道:“先问问他自己再说。不行,我们再帮他定就是。”
游拂成熟得早,经常去杜家,见过杜家的千金,心里早就有意,只是婚姻之事不敢擅自做主张。没有想到杜家上门这么快就提亲,听了父母的询问,脸倒红了,回答道:“双亲在上,孩儿但凭吩咐。”见孩子默许,游酢夫妇满心欢喜。
第二天,游酢请先生写了游拂的庚帖,便派人送帖并且去回话。杜家见游家答应了亲事,十分欣喜,连忙也请择日先生选好日子回了女儿的庚帖到游府。几天后,由管家出面牵线,游、杜两家父母在一家酒家见面,当面议定了孩子的婚事。但是,因为游拟还没有结婚,游拂也只是定个亲。
杜善只有一个女儿,不但给了女儿丰厚的嫁妆,而且准备赠送了一个大店铺。游拂定了亲,杜善就把游拂当做女婿看待,将一家店铺给了他,还帮忙着经营。从此,游拂在和州经商为生,成了一个有实业的小老板。
春末,游酢来到乌江视察春耕工作。经过功桥镇时,特地去丰山村拜谒瞻仰张籍的故居。张籍的后代不少已经迁往南方,只剩几户人家。由于张籍在世时一生贫寒,所居亦不过一般的民房,并无特别之处。询问起他的后代,有的竟然不知张籍是谁,只有一位老人尚且能够熟悉地背诵张籍的诗。游酢离开丰山之后,对知县说道:“世局如棋,一个人生前尽管多么的了不起,能够三代相传者稀少啊。”
他们到江边。这里山势险峻,江流湍急,波涛滚滚。乌江知县说:“这就是传说项羽当年自刎之处。”望着滔滔江水,想起“力拔山兮”的西楚霸王项羽,游酢临江感叹道:“项羽虽然失败未能坐江山,也算得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英雄。”
游拟回来了,他没有考中功名,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也不到吴家去。游酢知道他情绪不好,也不急着催办婚事。吴参赞那一头派师爷来提婚事,游酢回复:“过一段再说。”因此,此桩婚事又凉了下来。
四月初,遇到饥荒,和、含两县知县告急:县民缺粮,许多农民断炊,米行老板,奸猾的囤积不卖,眼光势利的乘机哄抬米价,有良心的只是多少略提一点米价;地方豪绅和财主怕官府会摊派故意装穷。有些买卖人见没有了生意,偷偷溜走。
游酢分析了当地的情况,传令各县一边去做好稳定生意人和市场的工作,一边动员富有者平价捐粜粮食给老百姓,官府给予适当的补贴,哄抬米价的现象被抑制住了。但是,全州粮食严重短缺,下面的各县确实无法解决目前的困难。游酢打算打开府廪赈救灾民,幕僚们认为不可以,再说府库储粮食不足,于是说:“灾荒这么严重,只好向附近的州县借借,渡过这个难关再说了。”一面传公文给周围的州县,不要限制和州人民的籴米,一面决定向其他州郡借取粮食分发给老百姓。他先派心腹到江苏、浙江等地借来了三批粮食。
没有多久,饥饿的人有了吃的,缺少粮食的得到了接济,逃走的听说后很快回来了。于是,老百姓再也没有人有出走的念头,和州的社会秩序重新得到安定。
没有料到这个问题刚刚解决,河北、河南逃难的难民每一天至少有几十人、多至上百人涌进和州地面。游酢听说此情况,亲自到地面上走走看,亲眼目睹街上、路边,到处站的、坐的、躺着的,拖儿挈妇,一个个面黄肌瘦,愁容满面,有的还哭哭啼啼,目不忍睹。大量的难民到来,也给当地的治安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许多当地居民的房屋食物被偷盗,有个别的难民大白天跑到当地居民的家,见有人就讨饭讨钱,见主人不在就进去偷吃,偷东西。和、含等县知县都出面劝难民回自己的家乡去,但是他们不走,而且难民一天比一天增加。诸县再次向州府告急。
游酢忙召集幕僚们前来共同商议解决的办法。分管治安的通判张文举问道:“游大人,这么多难民怎么办?”。有个幕僚说:“我们这里又不是避难所,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地盘不就了事了。”有的同僚说:“我们自己境内难关都难渡,管不了那么多。”游酢严肃地说:“传令下去,对于这些难民千万不能用粗暴的方式,他们本来就在受苦受难,如果再用粗暴方式对待,不等于往他们的伤疤上撒盐吗?天灾人祸,这是考验我们当官者的关头,他们虽然不是我们地方的百姓,但是同样是天子的子民,我们可是朝廷的命官啊。人命至为重要,一面先安置处理好,一面登记造册加以疏导、分离,派人动员回去。”于是,府里急忙下公文传令各县妥善先安置处理,将当地所有可用的空房腾出来,不够的安排到佛寺去住。
难民实在多,当时天气又炎热,瘟疫开始流行。诸县再次向州府告急。游酢写了:“以人为本,想方设法,疗食并举,治病救人。”十六字传下令去,各县于是一面给难民吃,一面到处请郎中给病人医治,自己县里郎中太少,还到外县请,和州百姓也配合官府出粮食出钱帮助,有的上山去采药,有的献出自己家藏的药物,结果救活的人不计其数。因为,和州的官府和老百姓的真诚与爱心,使难民们深受感动,不久都回去了。
俗话说:“林大鸟多”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和州虽然只管和、含、乌江三个县,人多事杂,当一个地方长官不但有繁忙的政务,而且也有一些头痛的小事。刚刚解决了难民的问题,接着又发生了一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欲知详情,下文解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