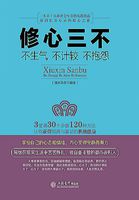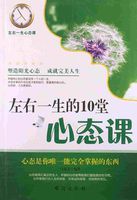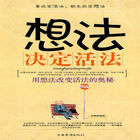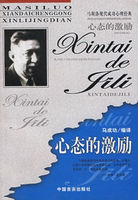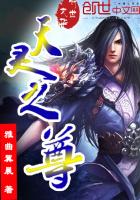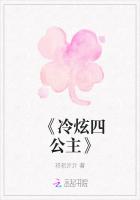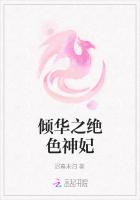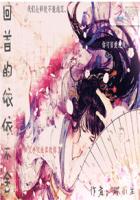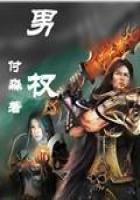提到妇人之仁,可能有点轻视女性的意味,首先我们要讲讲什么是“仁”。在《孟子》一书中,有个关于一头牛的故事,正好解答了这个问题。中国古代,凡是谈到君主帝王,大多都以龙来作比拟。但孟子和齐宣王见面,却大谈其牛,这是历史上较为有趣的事。然而这次谈话中。
讨论的是齐宣王不忍杀一头牛而改杀羊的事情。从这件事上,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仁爱是领导人行仁政的基本方法,但我们所提倡的仁爱是大慈大悲,而不是妇人之仁。
当时齐宣王看到一头牛在被杀前瑟瑟发抖,于是不忍心宰杀他,这种心理就是人类仁慈心理的根本。这种仁慈心理,在平时看起来,似乎人人都具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假如真正研究心理学,不论政治心理学,或者宗教心理学,齐宣王这个以羊易牛的故事,可以用一句大家都知道的俗语一“妇人之仁”来形容。因为女人容易掉眼泪,只要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难过掉泪。古人说“妇人之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人们的慈悲,不要走小路线,要大发慈悲,具大仁大爱,所以才用妇人之仁——
看见一滴血就尖声惊叫的“仁”来做反面的衬托。实际上妇人之仁,也正是真正慈悲的表露。正如齐宣王看见一头牛发抖便不忍宰杀,扩而充之,就是大慈大悲,大仁大爱。只可惜他没有扩而充之,而是以羊易牛而已。
唐睿宗李旦和哥哥中宗李显一样,都是唐朝曾经两次登上帝位的皇帝。在公元684年,武则天将中宗李显废黜,让李旦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这也是一个傀儡的角色。
武则天在李旦登基之后,下诏将年号改为“文明”,又将李旦的长子李成器立为太子。表面的文章做完了之后,李旦便被母亲安排到了皇宫中享乐去了,政事则由她继续把持。
到了六年后的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废掉了唐朝的国号,改成了“周”。李旦虽然被立为皇嗣,又赐姓武,但他的地位没有什么改变,还是个傀儡性的人物。
被姑姑武则天封成魏王的武承嗣很想代替李旦做皇嗣,准备以后继承姑姑的帝位。为了达到目的,他千方百计地活动,但武则天却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最终认清了立皇嗣的重要性,打消了立武承嗣为皇嗣的想法,这使武承嗣非常恼怒,于是收买武则天的贴身侍婢,让她诬陷李旦原来的刘皇后和窦德妃,说她们夜里常一起诅咒武则天。
武则天一听大怒,也不辨真假就下令将她们二人凌迟处死。
接着,武承嗣又诬陷李旦要谋反,在大臣们的极力劝说下,武则天才打消了制裁李旦的想法。命虽然保住了,但李旦却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对皇位的事没有丝毫兴趣,提出放弃以后的继承权。最后,武则天在大臣的建议下,将李显秘密接回来,立为皇位继承人,李旦则降为相王。后来,武则天病重时,大臣们发动政变,让武则天让出了皇位,李显即位。
到了公元710年,中宗李显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死,她们想立中宗的儿子李重茂做太子,由韦皇后主持朝政,像原来的武则天一样逐渐向女皇过渡。但还没等她们的计划实施,李旦的儿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就抢先发动了兵变,除掉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等人,李旦在他们的拥立下,再次登上了不再感兴趣的皇帝宝座。
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李旦处理得比较好。他的长子是李成器,但李隆基的兵变之功显然比他的哥哥要大得多。
这让李旦为难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李成器提出把太子之位让给弟弟,同时,大臣们也支持立李隆基。李旦在立李隆基为太子后,又封长子李成器为雍州牧,并兼太子太师,地位也很高。这样便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较好地解决了。
即位初期,李旦在李隆基和李隆基推荐的宰相姚崇的鼎力辅佐下,政绩颇为突出,在选官制度、平反冤假错案等方面都有所成就。
在即位的第二年,睿宗李旦便没有了原来的魄力,变得昏庸起来。在官员的选任上,不辨忠奸,将一些奸佞之臣提拔到了宰相的位置上,严重败坏了朝政n太平公主的梦想是像母亲武则天一样有朝一日做女皇,在李旦登基的第二年,通过争夺,利用李旦对他的信任,逐渐占据了上风,使李隆基丧失了主持朝政的权力,李隆基的得力助手、宰相姚崇和宋壕也被罢职。
李旦因为以前母亲的所作所为,加上自己所受的苦难,对皇帝这个人人喜欢的权位没有什么兴趣,一直想早点把皇位让给儿子李隆基,自己去做逍遥自在、清闲无事的太上皇。
公元711年,即李旦重新登基的第二年的二月,李旦传下诏书,要太子李隆基行使监国之权。两个月后,又召来三品以上的重臣商议传太子皇位的事。由于这时大多数的人已经倒向公主一派,所以没有人敢表示同意。加上公主一派的极力反对,李旦便采取了一个过渡的方式:太子全权处理政事,其他军国大事、死刑的批准、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免等,先与太子商议,拿出处理意见,再由他最后决断。
太平公主对此很不满意,一直想将李隆基除掉,扫除自己以后做女皇的一大障碍。在公元712年的七月,彗星在天空出现,这在封建社会时被认为是一种凶兆,所以,太平公主赶忙采取了行动:唆使一个术士向李旦说李隆基要篡位做皇帝了。没想到,这一招非但没有让李旦废黜李隆基,反而使李旦做出了马上传位给李隆基的决定。无奈之下,太平公主只好顺水推舟,建议李旦禅让皇位,但同时她又提了一个条件:由他掌握朝政大权。李旦不好让太平公主失望,勉强同意了。
公元712年的八月,李旦正式将皇位传给了太子李隆基,自己做了太上皇。在名称上做了严格规定:李旦自称还是皇帝用的“朕”,下的诏书叫做“诰”,每隔五天在太极殿听政一次,处理政务。至于李隆基则自称为“予”,下的诏书则叫做“制”或“敕”,以示区别,李隆基的办事地点在武德殿。另外,还对职权做了区分:四品以下的官员任免由李隆基来负责决定,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免则由太上皇李旦亲自决断。
睿宗的政治生涯是行妇人之仁的典型,首先他被武则天摆布,做了一个傀儡皇帝,自己还心安理得,不思进取,一点也不像个大丈夫,后来甚至一度让中宗李显再度登上皇位,好不容易经过一系列斗争,自己的儿子又把失去的皇位夺了回来,可这个时候睿宗又是优柔寡断,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之间摇摆不定。
仁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美德,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要打破这种观念的束缚,就要注意行事的时候不要抱着妇人之仁的态度。
陶朱公:错识人性,痛失爱子
性格是指人对现实中客观事物经常的稳定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比如说,有的人小心谨慎,有的人敢拼敢闯,小心谨慎与敢拼敢闯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人们根据他们外现出来的习惯化了的特征来判别这两种人的性格差别。
性格的形成固然会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在后天环境中磨炼出来的,而且定型之后,有很强的稳定性。一夜之间判若两人的情况多半属短期行为,是因为受到莫大刺激突变的结果;一段时间以后,固有性格又会重现,这就是因为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的缘故。性格成形稳定后,既不容易改变,对人的行为也会产生极大的支配作用。逆来顺受惯了的人,如果不经历大波折、大痛苦,是很难迅速转变成一个坚决果断的人的。即便由于这样或那样的机缘,这种人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时间一长,他多半还是会下来的。多年来的逆来顺受已使他对权力没有多大的欲望,而且他也习惯了受人支配(或自己动手)、不用支配别人的行为方式。像金庸笔下的张无忌,身上就带有这种特征。他的武功智慧都是一流的,却没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学成盖世神功纯属巧合,当上明教教主是因为形势所迫,最终他还是携佳人归隐山林去了。
但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阅历丰富后,鲁莽的人可能学会了适当的谨慎,勇而无谋的人可能学会了相时而动,这都是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发生若干变化的结果。
从性格上来识别人才,应充分把握其恒定不变的特征和后天环境造成的变化。准确把握人才的个性,是事情成败的重要前提。
陶朱公原名范蠡,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以后,功成身退,转而经商。后来辗转来到陶地,自称朱公,人们都称他为陶朱公。后来他的二儿子因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想用金钱赎回二儿子的性命,于是决定派小儿子带着许多钱财去楚国办理这件事。长子听说后,坚决要求父亲派他去,他说:“我是长子,现在二弟有难,父亲不派我去反而派弟弟去,这不是说明我不孝顺吗?”并声称要自杀。陶朱公的老伴也说:“现在你派小儿子去,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老二,却先丧了长子,可如何是好?”陶朱公不得已就派长子去办这件事,还写了一封信让他带给以前的好友庄生,并交代说:“你到那儿之后,就立即把钱给庄生,一切听从他的安排,不要管他怎么处理此事。”
长子到楚国后,发现庄生家徒四壁,院内杂草丛生,按照父亲的嘱咐,他把钱和信交给了庄生。庄生说:
“你就此离开吧,即使你弟弟出来了,也不要问其中的原委。”但长子告别后并未回家,而是想:这么多钱给他,如果二弟不能出来,那不是大亏?欲留下来听候消息。
庄生虽然穷困,但却非常廉直,楚国上下都很尊敬他。陶朱公的贿赂,他并不想接受,只准备在事成之后再还给他,所以那些钱财他分毫未动。陶朱公长子不知原委,以为庄生无足轻重。
庄生向楚王进谏,说某某星宿相犯,这对楚国不利,只有广施恩德才能消灾。楚王听了庄生的建议,命人封存府库,实行大赦。陶朱公长子听说马上要大赦,弟弟一定会出狱,而给庄生的金银就浪费了,于是又去见庄生,向庄生要回了钱财,并暗自庆幸。庄生觉得被一个小孩子欺骗,很是恼怒,又进宫见楚王说:“我以前说过星宿相犯之事,大王准备修德回报。现在我听说富翁陶朱公的儿子在楚杀人被囚,他家里拿了很多钱财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并不是为体恤社稷而大赦,而是由于陶朱公儿子的缘故才大赦啊!”楚王于是下令先杀掉陶朱公的次子,然后再实行大赦。结果陶朱公的长子只好取了弟弟的尸骨回家。
长子回家后,陶朱公悲泣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一定会杀死他弟弟的!他并非不爱弟弟,只是因为他年少时就与我一起谋生,手头不宽绰,所以吝惜钱财。而小儿子一出生就看见我十分富有,所以轻视钱财,挥金如土。以前我要派小儿子去办这件事,就是因为他舍得花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