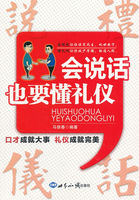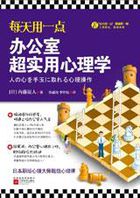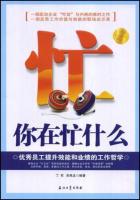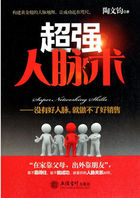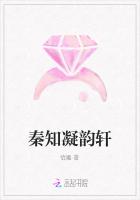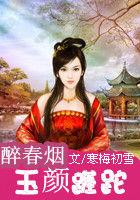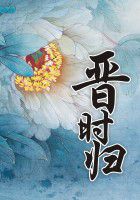唐玄宗时代的“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则是“得贤则安,失贤则乱”集中地反映于一人之身的典型事例。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子,生值武则天后期及韦后专权时代,幼受宫闱政治斗争的熏陶,养成果敢练达、聪敏机谋的禀性。先是率羽林军杀韦后,拥立李旦复位,继之于公元713年即位,铲除太平公主及其死党,真正握有政权,开始了他一生极富戏剧色彩的政治生涯。
唐玄宗的政权是在火与血中诞生的,因此,他深知权力来之不易,登基之初便摆出了一副开明君主的姿态。在用人方面,表现为知人善任、尊崇贤才、从谏如流。史载,韩休为人刚毅正直,一心为公,不为功利所动。做丞相期间,韩休与玄宗心息甚通。玄宗每觉有错,便问左右:“韩休知否?”刚说不久,韩休的谏书便呈了上来。
有人问玄宗:“韩休为相,陛下殊瘦如旧,何不逐之?”玄宗感叹地回答:“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常顺指,既退,吾寝不安;休常力争,既退,吾寝乃安。吾用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
在清醒知人的基础上,唐玄宗用人甚有主见。开元初年,玄宗打算任命姚元之为丞相,引起中书令张说的不满。于是,张说先是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弹劾姚元之,遭玄宗斥退;继之又命殿中监姜皎诱劝玄宗,欲使姚元之出任河东总管,反被玄宗识破,斥之曰:“此张说之意,汝何面欺?”任命姚元之为相的初衷未稍有改。
唐玄宗既知贤,也敬贤。姚崇、宋理一心向公,聪明练达,玄宗视之如同唐初名臣房玄龄、杜如晦,每次进见,玄宗都要站起来相迎;离去时,则要临门相送,其敬贤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玄宗前期知人善任,礼贤有加,在他的周围聚集起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如姚崇、张嘉贞、张说、李元绂、杜暹、韩休、张九龄等,皆一时俊杰。唐玄宗前期大量人才的涌现及使用,直接促成了“开元盛世”的出现,史称开元年间,“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
唐玄宗毕竟没有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天下太平之后,遂在生活中贪图享受,政事上疏于怠倦,早期的进取精神被时间慢慢地磨光了。在用人方面,越来越爱听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辞。于是,一批野心家和佞邪之辈得到任用,尤以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为最。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的叔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善于察言观色、阿谀逢迎。他利用皇家贵族的优势与方便,交好宦官和嫔妃之家,打探皇帝的动向,在他任礼部侍郎时,每次上书奏事都能贴合皇帝心意,从而博得皇帝的信任和喜爱。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升任丞相。为达专权之目的,李林甫一方面排斥异己,广结私党,大批贤能忠直之士因此或遭贬或被杀;另一方面杜塞言路,掩蔽皇帝。例如,有一次李林甫威吓众官说:“你们有没有见过平时作仪仗用的马匹呢?只要乖乖地按指令行事,可以吃到三品料食,一旦嘶鸣起来,马上就被赶走,后悔都来不及呢。”自此之后,玄宗更听不到对李林甫的批评了。
杨国忠系杨贵妃之兄,玄宗爱屋及乌,不问忠奸贤愚,遂使杨国忠得以步步高升,天宝年间任右相,兼40余职,权倾内外。
杨国忠为巩固自己的权势,内则哄骗欺蒙玄宗,外则打压异己,致使朝廷之上忠义者少,奸佞者众,吏治日坏。此时的李隆基已堕落成一个浑浑噩噩的寄生虫,明皇之风荡然无存了。
唐玄宗早期到晚期用人政策的蜕变,直接促成了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的爆发。玄宗用人失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对边帅的任用与管理不当。唐初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平时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战时则受命出征。自开元时起,改为募兵制,允许边将招募兵卒,渐渐形成边帅拥兵自重的形势。加之玄宗为开边需要,使边将10余年不换,边镇节度使几乎成为世袭。
李林甫还建议玄宗任用胡人为边帅,安禄山便借此登上了中唐的政治舞台。安禄山为人狡诈,但外貌痴直,玄宗曾指其大肚皮问道:“腹中何有?"安禄山乖巧地回答说:“更无余物,止有赤心耳。”如此之类博得玄宗的欢心,以为忠诚之将。直至安禄山磨刀霍霍时,玄宗还一味信任,并有以之为相的打算。由于玄宗任人失察,最终酿成大祸。
史家在论及玄宗的用人政策时,曾有十分精当的评价:“开元之初,励精图治,几致太平,可谓盛矣;天宝之后,奸臣执权,艳妃乱政,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玄宗之谓也。”
综观人才得失与国家安危的鲜活的历史画面,我们不禁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喟:对于历代统治者来说,不管其基业如何雄厚牢固,也不论其自身才华如何超群绝伦,只要他以才自恃,缺德妄行,亲小人而远贤才,等待他们的只会是自取灭亡。
得贤则安,失贤则乱,既是必然,同时也是一个过程。不能简单地企盼任用了一批贤才,各项事业便会在一夜之间焕然一新;同样,失去了贤才,由于其原有的良好基础,各项事业也未必会短期内一塌糊涂。这当中确一个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问题,但是,量变的结果必然会引发质变。
忽必烈:充分授权,放心任用
在元朝统一中国以前,还从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像蒙古族那样成为统治全国的民族,领导蒙古族完成这统一大业的元世祖忽必烈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忽必烈从蒙古国大汗而跃升为全国的皇帝,并将元朝的局势逐渐安定下来,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华。
那么,忽必烈又是凭借什么手段,将原本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元王朝治理完善的呢?其中一条重要的秘诀就是他善于授权,任用各种人才,让他们各负其责,从而使统治权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忽必烈授权绝不是盲目进行的。在进行授权之前,他会对被授权者进行全面考察,只有觉得其人确有才能,而且对自己忠心耿耿时,才会充分授权,放心任用。
被誉为元代创基“首功之臣"的刘秉忠,就是先由得到忽必烈非常器重的海云法师的推荐,与忽必烈多次交谈之后才受到赏识的。刘秉忠成为忽必烈的谋士后,尽忠竭虑,诚心辅佐,成为忽必烈的股肱重臣,为元朝的建立立下了卓著功勋,其中之一便是全权负责营建大都。
蒙古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定居的习惯。早在蒙哥当蒙古大汗时,忽必烈就举荐刘秉忠设计、营建了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初年也以此为统治中心。但是随着元朝疆域不断向南扩展,统治中心也相应要求南移。
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决定以中都为首都,改称大都,即今天北京城的前身。
这个决定作出之后,忽必烈又委任刘秉忠主持新都城的设计和营建工作。刘秉忠召集了许多专家,按照古代都城结构的传统,以“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思路设计出新都城的规划。这一设计很快就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
新的都城气势宏伟、整齐划一,打破了汉唐以来的坊市封闭形式,使整个城市显得更加开阔而富有生气,体现了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气势。因此都城刚一建成,以刘秉忠为首的参与人员都得到了忽必烈的奖赏,刘秉忠也因此更加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和信用。
忽必烈虽然以一个游牧少数民族的首领而入主中原,但他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元代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忽必烈的召见,最终建立了一番功业的。
郭守敬生于一个科学世家,其祖父郭荣就精通算数、水利,郭守敬从小就受到熏陶,成年后在天文、数学、仪器制造和水利工程等方面深有研究。在一次随祖父到磁州紫金山研讨学问时,郭守敬得以结识朝廷重臣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人。
当张文谦升为左丞相后,忽必烈要求他推荐懂得农田水利的专家,张文谦当即就推荐了郭守敬。忽必烈大喜,很快就召见郭守敬。
郭守敬见过忽必烈,提出了发展华东平原水利工程的六项建议,每条建议都有具体的实施方案,甚至连所需要的人工、物资都计算出来了。
忽必烈听了郭守敬有条有理的介绍后,心中大喜,因为他需要的正是郭守敬这样的人才。于是忽必烈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像郭先生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办事的人!要是所有人都能像郭先生这样,国家怎能治理不好?”于是当场委任郭守敬为副河渠使,总管各地的河道水利事务。
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前往西北地区修复河套平原的渠堰。经过三个月的辛苦工作,河渠工程终于完成,不仅航行便利,还能灌溉良田九万余顷。当地人民为了纪念郭守敬的功绩,还在渠上给他建了座生祠。
从西夏归来后,张文谦再次向忽必烈举荐郭守敬:
“陛下,郭守敬的确是一位才能出众的治水专家。现在中原水旱为患,治理河川、兴修水利是当务之急,望陛下能够重用郭守敬。”
忽必烈再次召见郭守敬,询问兴修水利之事。郭守敬面陈十一件水利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修筑通州至大都的运河。在郭守敬的主持下,这条运河于1293年建成通航,这就是著名的通惠河。据说运河竣工放水这天,忽必烈亲自登上河堤,看着大大小小的运粮船只沿运河鱼贯而行,心中大喜,立即传旨赐郭守敬二千五百贯钱,次年又拜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院事(掌管天文、历法等中央机构的副职冒员)。
除了兴修水利之外,郭守敬还与许衡‘王恂等学者合作,于1280年修成新的历法——“授时历”。这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采用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天文常数值,证实了一年的日期为365.2425天,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6秒,这在世界历法史上还是第一次,比西方通用的格利哥里历早了300年。
除此之外,郭守敬在天文观测、数学、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郭守敬成就的背后,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忽必烈慧眼识英才,并且善于充分授权的作用。因为在封建社会,如果没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像郭守敬这样的科学家也许会失去良好的研究条件,那么他所能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必将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说,忽必烈的识才与授权又是多么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