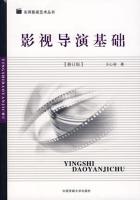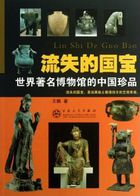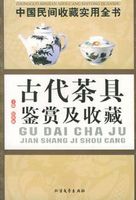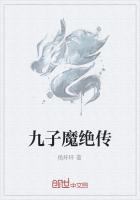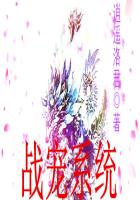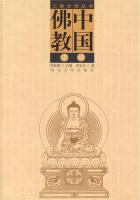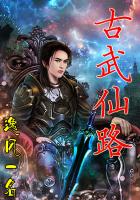话本逻辑与“说书人”传统
在第一章中,笔者曾论及以诗文传统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戏剧叙事,对影像叙事所造成的规训与制约,以及影像叙事对此形成的粗浅的解构与重构。其实,究其更深的根源,在传统戏剧叙事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具体的叙事逻辑,它不仅决定了中国传统戏剧叙事的主要框架,也几乎决定了其他传统叙事形态的主要面貌,它虽然只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样式,但却似乎成了所有传统叙事形态的通用准则,无论是戏曲还是其他的艺术都受到它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所代表的叙事框架,暗含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与教化指向,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叙事手段,而是上升为某种含有意识形态意义的叙事逻辑,即所谓的“话本逻辑”。中国传统戏剧叙事的基本形态说到底也是“话本逻辑”渗透的结果。
根据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所定义的话本概念,“话本,在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说来,应该是,并且仅仅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5页。)其叙事结构基本上包含了四大部分:入话、头回、正话以及篇尾。所谓“入话”大体上是以诗词入话,或引用古人的,或写作者自撰的。这些诗词基本上与后面的正文有着直接的关联。当然,入话并非完全无的放矢,从它与正文的关系来看,它还可以起到营造意境、培养情绪、抒发感慨、点题引题的作用。“头回”也是话本叙事的独有模式,“在不少话本小说的篇首,有时在诗词和入话之后,还插入一段叙述和正话相类的或相反的故事。这段故事,它自身就成为一回书,可以单独存在,位置又在正话的前头,所以叫做‘头回’。亦称‘得胜头回’、‘笑耍头回’。”(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8页。)就说书现场而言,头回的主要功用在于拖延时间,以等待更多的听众。就结构而言,无论其与正文之间性质相近或相反,都是一种理解叙事主体的辅助性手段。所谓“正话”,便是话本的主体部分,是铺展情节、塑造人物和描写环境的主要载体,就其形态而言,与现当代小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在叙事结构上,大部分的话本都采用一种预警式的叙述方法,即话本一开始就指向一个特异的结局,直接预示人物的命运。譬如“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之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毫不隐藏、简明扼要地概述了故事的开端、发展与结局。同时,在正话的展开过程中,说书人不断地介入到事件里边,打断叙事的节奏,发表自己对事件、人物的看法,与听众进行交流,将叙述主体与叙述客体都处在自己的控制之中。“篇尾”是整个话本的结局,却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说书人对所叙述的故事的总结和交代,它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附加部分,在形式上跟入话一样,以诗词的形式呈现,说书人借以发表总结性意见,进行职业化的表演,展示他对故事的主观性理解和把握,或评论,或劝诫,但总体上都离不开符合封建意识形态的说教。
从宋元到明清,这四大结构成了一种话本演绎的逻辑,无论是拟作者的文字叙事,还是说书人的口头叙事,乃至根据话本演绎而成的戏曲叙事,都要严格地遵循这一逻辑。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在话本的四大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圆环的关系,从头至尾,都穿插着一条隐形的链条,即符合民族意识形态规训的独有的叙事美学。头尾呼应,框架清楚,层次分明,不管叙述过程如何散漫、碎化,但整体的叙事结构都必须显示出一种近乎圆形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其实是中国深厚的农耕文明的显现,根深蒂固的自给自足的文化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对叙事艺术的圆转完满的形式诉求,也造成了民族叙事的惯常模式,无论是话本还是戏曲叙事,都是对这一模式的遵循。
而根据陈平原的研究,早期话本是一种相对单纯的说书艺术,无论是叙事还是价值取向,都要生动活泼得多。但文人创作的介入,使话本开始逐渐脱离说书传统,成为真正的案头之作。他认为,文人独立撰写的小说,与根据说书艺人底本改编者最大的差别,莫过于后者重情节而前者求教诲。小说家们显然更醉心于惩恶扬善的说教,大段大段地发表未必十分精彩的议论,这样,“说书艺术”逐渐被文人自以为是的“道德文章”所取代。就像自怡轩主人在《娱目醒心编序》中所称的:小说,“既可娱目,亦以醒心”,不管是忠孝节义,还是因果报应,都必须“隐寓于惊魂眩魄之内,俾阅者渐入圣贤之域而不自知”。(陈平原:《说书人与叙事者——话本小说研究》,《上海文学》1996年第2期。)然而,比较反讽的是,虽然文人与说书人分属于两个不同场域的掌控者,但是不论文人的介入如何充分,在与说书人的权力较量中,仍然处于下风。因为他们在文本场域“未必十分精彩的议论”要想获得近乎十分广泛的道德教化效果,必须依赖说书人的现场评说。案头之作毕竟属于精英化创作,其接受群体也相对有限。唯有说书人掌控大局的书场,才能与戏场一样,直接面对广泛的“受教”群体。说书人恍若现代沙龙中的主持者,堂而皇之地引导着文人意识形态的传播指向。因此,在话本的叙事权力格局中,说书人作为一种“代言人”,却扮演着比著者更加显要的角色。故而也可以这么认为,恰是在文人对说书艺术强势介入、日益把话本逼向案头文学的同时,说书人却因为与文人意识形态的联姻,其在场优势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进而发展成为民族叙事的一种传统,渗入到随后的各种叙事艺术之中。甚至连文人最后都不得不“屈服”于说书人的权力,在其创作的拟话本和后来的长篇章回小说中,把说书人作为故事的叙事主体和最权威的叙事成分,统领文本的写作过程。显然,这是文人主动的有意识的妥协结果,假借说书人的口吻传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说教。说书人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叙事艺术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和格调,造就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叙事范式的特殊体制,并严格规训着叙事艺术的创作思维与读者的审美观念,乃至上升为更高的涉及民族意识形态的层面。譬如,话本脱胎于古老的史传传统,对真实性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对虚构性的需求,这其实体现的是一种民族化的叙事态度。与西方叙事对虚构性的坦然不同,具有史传传统的叙事艺术总是害怕堕入虚构(欺骗)的质疑中,极力以各种证据与理由来证明叙事内容的“确有其事”。这虽然是中国传统叙事艺术尚不发达的表现,其实也体现着民族意识形态的规训:事若不实,如何能证明作者的道德品性,如何维护作者的文化权威,又如何能载道立言,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引导人遵从封建道德礼教与官家意识形态?是故,说书人在开场与篇尾中,总是要以某某名士“所见”、某某名士“亲闻”,或直指故事的发生地点、时间等来佐证故事的真实性,甚至打断叙事的流程,插入另外一段恍若亲见的故事来增强主体故事的存在合理性。
电影《难夫难妻》,1913年,导演:张石川
由此,也不难想见,几乎与宋元话本同时兴起的宋元杂剧,以及之后的明清戏曲,之所以表现出同样的叙事美学特征,也正是基于这种“说书人传统”的需求。话本叙事中的说书人传统,以打断叙事进行道德评说的演进方式,在宋元杂剧乃至后来的明清戏曲中,是以众多的插科打诨的形式出现的,说书人也常常出离于主体叙事之外,以一种调侃的方式,完成道德评说的任务。所以,不论艺术形式是否发生变换,话本的叙事已成为一种逻辑,与衍生出来的说书人传统一起,作为一种民族叙事体制的表征,深深地影响着民族艺术的叙事范式,乃至某种试图获得民族文化身份,参与民族审美秩序的“外来艺术”,比如后来的“影戏”。且不说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的《定军山》就是对京剧表演片段的简单记录,8年之后由亚细亚公司出资发行,新民公司负责具体拍摄的影片《难夫难妻》,虽然由郑正秋与张石川导演,但所有的演员却都由文明戏的演员担任,甚至因为当时有男女不能同台的戏曲规矩,连片中的妻子也由男演员充任。影片拷贝虽然已经丢失,但我们根据一些时人的口述还能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首先,就影片的叙事内容而言,它是郑正秋根据他家乡潮州的乡俗风情撰写而成,讲述了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被逼成婚的故事,入话、头回、正话以及篇尾等基本段落赫然在列,整个叙事框架几乎是对话本结构的严格遵循;其次,相比《定军山》,《难夫难妻》的拍摄手法依然没有产生什么技术性的飞跃,按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中的说法:“导演技巧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摄影机的地位摆好了,就吩咐演员在镜头前面做戏,各种的表演和动作,连续不断地表演下去,直到200英尺一盒的胶片拍完为止。”“镜头地位是永不变动的,永远是一个‘远景’……倘使片子拍完了而动作表情还没告一段落,那么续拍的时候,也就依照这种动作继续拍下去。”(张石川:《自我导演以来》,《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从某种意义上说,《难夫难妻》其实是一出文明戏的完整复制,更谈不上所谓的电影语言,说到底还是“讲述”传统在“影戏”中极为顽强的保留。
当然,民族叙事中的话本逻辑与说书人的“讲述”传统也并非一成不变。它们必然也要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以及叙事艺术的逐渐成熟,发生相应的转移。综观中国叙事艺术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细微却真实的轨迹:唐传奇的叙事主体是作者本人,最多是作者与叙述者并存。到了话本阶段,作者开始退场,代之以说书人和叙述者在场。最后,连说书人也逐渐退出文本,只剩下叙述者充当故事的见证人,并最终引发了非说书体的现代小说的出现。这一发展轨迹,其实与西方文论所强调的叙述观念殊途同归。西方文论根据叙事成分在作品中介入程度的不同,将叙事艺术分为“讲述”和“展现”,认为“讲述”的叙事作品中作者主观介入过多,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感,而“展现”的叙事作品则排除了作者的主观意识,所以是“客观”的,真实性更强。这种认识渊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纯叙事”和“纯模仿”的区分。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将叙事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诗人,“以自己的名义叙述,而无意使我们发现并不是他本人在叙述”,即“纯叙事”,另一种是“诗人竭力造成不是他本人在说话”,而是某一个人在说话的假象,即“纯模仿”。一般而言,推崇“展现”的小说,都反对通过作者这个“中介物”来“讲述”故事。可以说,从“讲述”向“展现”的转移,是叙事艺术的发展规律,中外皆然。因此,中国叙事艺术的变化轨迹,也可以视之为一种对“主观”向“客观”、“讲述”向“展现”转变的追求。具体而言,这种由“主观”转向“客观”、由“讲述”转向“展现”的标志是:作者对故事的公开介入开始减少甚至基本消失。“看官听说”、“话说”、“且说”、“却说”这一类“讲述”故事的固定用语使用频率降低与“展现”相关联的描写手法增多。譬如《儒林外史》,除了在开头与结尾保留了“话说”和“且听下回分解”,尚存一丝说书体小说的痕迹之外,故事的叙述,人物的描绘,几乎全部采用客观叙事的方法。表现在:其一,说书人完全消失。我们再也听不到说书人常用的“看官听说”的招呼语,更没有说书人那些冗长的道德说教和议论。故事接受者再也不是听凭那个权威说书人任意调遣的“听众”,而真正成为具有独立思维的“观看者”,他们靠自己的思维逻辑从作者提供的客观画面中做出哲学的或美学的价值判断。其二,《儒林外史》的叙述者主动放弃了“全知全能”的无限权力,宁愿做一个冷静的、不动声色的“旁观者”,用纯客观的态度“展现”生活的场景或人物。如第一回写王冕放牛时看到三个头戴方巾的人在村外树荫下喝酒的场面:“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这三个人姓甚名谁,在说书体小说里,说书人或叙述者肯定要忍不住直言相告,但在这里,叙述者恍若不知,只以“胖子”、“胡子”、“瘦子”相称,不加任何判断地记录下他们的全部谈话内容。在这一场面描写中,叙述者像是一个置身场外的“偷窥者”,只依靠自己的视觉功能看到“胖子”、“胡子”和“瘦子”,依靠自己的听觉功能听到他们的谈话,此外便无意告诉读者更多的东西。这种叙述者全知能力的自我限制,在真正的说书体小说里,是基本不存在的。(孟昭连:《作者.叙述者.说书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主体之演进》,《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4期。)而这样的叙事方式又几乎与影像叙事类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