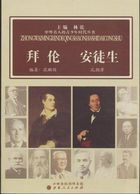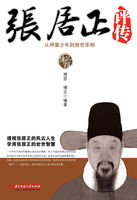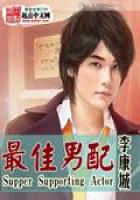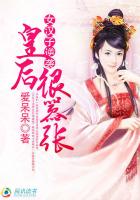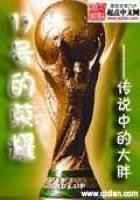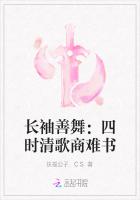毛、周、朱辞世——我对接班人的思考——对“唯生产力论”批判之批判——对华国锋上台的思考——“文革”闭幕与《毛选》第五卷——1978年上半年我在政协论述人治与法治,波及毛泽东功过是非及“文革”之评价——对我进行最后一次批判——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问: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革”闭幕。梁先生可否谈一谈在这个不寻常的年头里,有哪些思考、言论和行动?
答:1974年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我进行将近一年的批判斗争结束之后,我又进入对什么都保持沉默冷观的时期。我本人主要在家,每周仍去政协参加学习会两次,别的场合很少去。我对国家大事的了解,主要来自当时独具权威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在政协听到的文件传达以及为数不多的“小道消息”,因与他人交往少,小道消息故不多。
这一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1月9日早晨,电台广播这一噩耗。这一天上午,正是政协直属小组学习的时间。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这期间的学习内容,按上边布置,是批判“以三项指示为纲”,虽还没有明确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实际运动已经开始。矛头所指,邓小平之上,即周恩来是也。但又不明白点出,大家未经言传又都可意会,此乃“文革”中经常运用的绝妙战法之一。但政协直属组的全体学友们,对此不仅不热衷,且满腹狐疑,忧心忡忡。正传说周恩来病重,突然一声霹雷,能不使人震惊吗?而且偏偏发生在这种严重的关头。
经政协直属组召集人于树德、赵朴初、王芸生、王克俊商定,并征求全体组员一致同意,先把规定的学习(即运动)任务放在一边,转入对周总理的悼念。1月9日这天的学习会一开始,大家首先起立默哀,即有不少人失声痛哭。老学友们几乎都是年逾花甲或古稀之人,一生中都无例外地饱受忧患和磨炼,这眼泪怎能轻弹?全因为突然失去多年来所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之故。头一个发言的是申伯纯,他未曾开言即泣不成声,半个小时的叙述中,竟泪流数次。申老是政协副秘书长,中共老党员,也是当时政协直属组唯一的一名中共人士。除他之外,都是无党派人士,其中多数人在旧中国属国民党方面,都曾身居要位。申老早年也是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手下的一员,曾在1936年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出过力。他与周总理的相识和交往,即从“西安事变”开始,他断断续续、如诉如泣地回述着往事……
政协直属组对周总理的缅怀活动延续了一两个月的时间,要把全组二十余人的发言都写出来,当是一篇颇有史料价值的好文章,只是篇幅恐怕太长了一点。在这里我只介绍两点,以此概括全貌。
第一点,是全组人员都同周总理有过多次交往和接触,友情,教诲,都非一般。我只是点一点该组主要成员的名字和履历,便可以知道个大概了。如王芸生,国共和谈时他就是《大公报》的总编辑,那时就同周总理有交往;于树德,老同盟会会员,20年代初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又是共产党员,“五四”运动之前就在天津与周恩来相熟了;杜聿明、宋希濂,在黄埔时期就是周恩来的学生;程思远,跟随李宗仁先生多年,他最清楚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周总理花了多少心血;还有赵朴初(佛教界知名人士)、王克俊(傅作义行辕的秘书长)、范汉杰(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君迈(国民党长春市市长,赵恒惕之弟)、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创办人)、郭有守(国民党四川省教育厅厅长、外交官)、杨公庶(杨度之子),等等。他们每个人的发言,都是追思周总理丰功伟绩的一篇好文章。
第二点,是史良的丈夫、国际法专家陆殿栋先生,他缅怀周总理的发言安排在最后。陆不到七十岁,但有高血压。在别人发言的时候,他就常常激动、难过得流泪。轮到他自己了,刚刚讲了解放之初他到外交部工作,周总理是如何同他亲切谈话时,便突然言语不清,靠在沙发上。医院的救护车很快赶到会场。医生说是情绪过于激动,脑血管破裂。等史良本人闻讯赶到现场时,他已不省人事了。学习会当然只好中止,大家一直在会场里守着他,看着医生进行各种办法的抢救,但始终无效,终于停止了呼吸。
政协直属组缅怀周总理的活动,竟是以一位追悼者的去世而告一段落的。大家的心情更沉重了,谁都觉得事已至此,除了长歌当哭,还有什么可说呢?
问:后来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相继去世,政协直属组是否也这样自发地举行追悼、缅怀活动呢?梁先生也都作了发言吗?
答:情况有所不同。
朱德委员长于七月间去世。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其整个的悼念活动规模就很小,而且不久发生唐山大地震,学习活动因此停止了一段时间,政协直属组没有就朱德的辞世搞过悼念活动。
毛泽东主席的去世震动当然也很大。追悼规模很大,活动由全国上上下下统一组织,政协直属组也不例外。大家都分别被安排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等重要追悼活动,政协直属组本身还来不及考虑作较详尽的缅怀毛主席的发言,如对周总理那样,就发生了粉碎“四人帮”这样的大事。情况发生了突变,大家也就如同结束了一场长长的噩梦,从悲痛中醒来,进而喜悦、欢呼开了。
至于我个人,无论是周总理,还是毛主席,他们的去世,都是很悲痛的。但我的发言都不多,不长。我想得更多的是他们辞世之后,国家、民族将会怎么样?中国往何处去?这正是当时全国不分男女老少都最关切的事,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非想不可。我本人这时期更多的是自己想,很少说,不是不敢说,而是没有把握说。因为现实的变化太复杂了,局外人不可捉摸。
问:那么,从现在回头看,梁先生当时最关切的又是什么呢?能不能具体谈谈?
答:不必太具体了,因为许多问题早已得到解决,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只有一点可以说,那就是毛主席最操心又最难以解决的接班人问题。一个国家,若以法治国,则不存在选某个人来接班的问题;只有以人治国,才会考虑谁接班合适或不合适之事。这个是非,暂不议论。从事实上看,毛主席始终为接班人问题呕心沥血的。他先选中刘少奇,认为不合适了,才发动“文化大革命”,选了林彪;而后林彪自我爆炸,最可靠的接班人“告吹”。时至1976年,周恩来去世,天安门事件发生,本来亦由毛主席再度起用的“人才难得”的邓小平,又再度打倒;而毛本人又重病在身,怎么办呢?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排位子,按“当过兵打过仗,当过工人种过地”的条件,王洪文这时自然成了接毛主席班的最佳人选。但王实在无论党内党外都没有威望,是完全靠“文革”起家的,与姚文元差不多,连江青、张春桥那样的资历都没有。况且这几个人明明白白是连成一气的。在周总理去世,邓小平被批判之后,大家最关切的正是这个接班人轮空、后继无人的问题。我的心情也是这样,这就是不管选接班人的做法是如何不合法治国家的原则,但在当时中国的状况,如若选错了人,国家和人民将会更加遭殃的。但这件事,在当时,除了毛主席,谁都不敢说,不好说,谁都搞不清毛主席心里想的是什么。
天安门事件一发生,一方面,邓小平下了台,那当然是很冤枉的,毛主席又铸成了一大错;另一方面,毛主席却又自己否定了王洪文的接班,出其不意地举出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放在王洪文之上,华又兼任国务院总理。当时大家的心情,沉重、矛盾、困惑,什么滋味都有。对华国锋也了解很少,但总认为与王洪文不同,华比王当接班人会好些。至于毛主席为什么这么做,这又是一个谜。
问:梁先生,这个问题您当时有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提出来过?这一时期您都有过什么公开的言论?
答:我的公开言论那时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发表,那就是政协直属学习组。但我这时候说话最少。唯一在学习会上讲过几句话发过一点议论的,是关于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问题。所谓唯生产力论,已经被臭骂了若干年,什么“反动的”,“反革命的”,“黑谬论”,等等。我在会上就此发言说,报上许多大批判的文章,一概把“唯生产力论”臭骂一顿,实在没有必要,我不明白真意思是为了什么。其实,据我自己粗浅的学习体会,马克思主义学说一开始就把着眼点或者叫基本点放在物上,生产力上,所以叫做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根本。马克思、列宁都把物放在第一位,斯大林当政三十年,又何尝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把物放在第一位呢?我不明白,这“唯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何区分?特别是“唯生产力”竟成为一种罪状,仿佛发展生产力也是大错特错的事。果真如此,没有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高度的物质基础又从何而来?我的这段发言不长,并没有多加发挥。发言后遭到一些人的指责,说我是在放毒,名为不赞同臭骂“唯生产力论”,实则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辩护!不过这次没有连续批判,说了几句也就完了。因为这时大家的心思更加不在这方面了,远不及两年前“批林批孔”那样,至少还硬是说了又说,批了又批。大家都在困惑中逐步觉醒,似乎都心照不宣地有一种预感,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文革”已经临近尾声了。这种虚张声势而又极不实事求是的大批判,再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那时候,大家连表面文章都不想做下去了。
当然,我说的是当时参加政协学习的大多数人的心情。对于身居这类学习(实则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地位的少数人而言,则又不得不表示紧跟的姿态,其中有的人同样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亦有人另有目的,积极性还颇高呢。即以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为例,我的言论不足道,发言最系统而明确持不同意见的是杨东莼同志。杨是民进中央的负责人之一,又是中共党员,章士钊先生病故后由他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他同我不在一个学习小组,但那时常召集由各学习组参加的联组会,他在大会上作长篇发言,引经据典,说“唯生产力论”这一怪名词不知是出于哪一位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家之作,还是哪一位自命马列“秀才”者所杜撰。他以问题求教于参加学习的诸公,又明确表示对时下批判“唯生产力论”种种不理解,不苟同。杨的发言显然招惹了上头某些人的不满,接着便布置大会小会会上会下与杨辩论,想与两年前“批林批孔”时对待我那样热闹一番。只是的确这时候的气氛已大不及以往了,始终都没有能像模像样地搞起来。
问:毛主席病逝,“四人帮”被粉碎,宣告了“文革”的闭幕。梁先生其时心情和情况如何?
答:毛泽东主席是新中国的缔造者,近代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伟大人物之一。他的去世,人民举国同哀是情理之中的。但他晚年的错误,即使在当时,也已十分明显,只是大家不愿说、不敢说而已。林彪、江青之流能如此得志猖狂、施虐达十年之久,毛泽东自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采取果断的措施,彻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乃天理昭昭、四海归心之举!人民载歌载舞,普天同庆,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如同小孩子一般,兴高采烈地走出家门,加入了群众狂欢的行列。这可是多少年来所不曾有过的场面,人们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当是最确切的比喻了。
我也是这种欢欣鼓舞的心境!但兴许是老于世故吧,脑子里考虑得更多的是中共的路线政策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比方说,我最关心的阶级斗争这个老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究竟是如同“文革”那样,长期斗下去呢,还是改变旧道,另谋新路?慢慢儿,我注意到了,“四人帮”抓起来了,新的主席兼总理华国锋上台了,这当然是可庆幸的事。但遗憾的是路线、方针、政策似乎并没有大的变化。在理论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实践上,对“文革”没有丝毫的否定,甚至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也照样出现在报刊和街头巷尾的大标语牌上。特别是华国锋上任后所作的大事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使我更加深了自己的观察,对现实不可过于乐观,中国今后前进的道路依然存在着种种阻力。
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当时发行成百上千万册,影响很大,梁先生那时有着哪些印象和看法?
答:我要申明的是,我对《毛选》第五卷有看法,并不是因为第五卷中收有《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与我个人直接相关之故。而是整本选集,都是在“左”的指导思想下编选的。
不必一篇一篇地去细说了。在全书首页的《出版说明》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毛泽东同志是在反对什么什么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中包括所谓“反对彭德怀、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说明》还指出,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是“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创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正是在这个指导思想的指导下,才编选了诸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批判刘少奇、批判“右派”进攻等一系列的文章。应该指出的是,《毛选》第五卷中的多数文章的基本论点还是正确的,但因为编选者的错误指导思想,才出了这个偏差。
说到那篇批判我本人的文章,我觉得有两点要说的:一是有一些内容在我记忆中并没有,不知是怎么加进去的;二是本来是毛主席的许多插话,不是在一天讲的,现在串起来变成一篇完整的讲话和文章了。1953年发生的这件事,前边我已专门谈过。因此对这篇文章内容的是非曲直,在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毛选》第五卷出版的时间是1977年上半年。这桩事告诉我:“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人们对许多问题的错误认识却不可能很快得到澄清,真所谓积重难返呵!由于我是一个多年来都肯用心思进行独立思考的人,面对这一实际状况,便开始寻求一些重大问题的正确答案了。
1978年2月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十多年来不曾开过的盛会。出席会议的人,大多在会上回顾了“文革”中的遭遇,欢庆迎来了“第二次解放”,但偏偏对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制定新宪法,讨论得不多,研究、推敲得不够。我对此很不以为然,便以实际行动在大会期间的小组会上,提出建国三十年来主要是人治和今后则不得不走向法治这一十分严肃的问题。要论述这个问题,自然要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毛主席的功过,而在当时,这正是只允许说赞同话,而不允许持不同意见的敏感问题。我的发言立刻在会上遭到批判,而且在大会结束之后,继续组织以政协直属组为中心的原班人马,与我名为辩论,实为批判。批判进行的规模、情况与方法同1965年、1974年那两次相仿,只是时间短,火力弱,犹如强弩之末。因为接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批判会中途草草收场。
问:梁先生,您能回顾一下这次受批判的情况,特别是您当时的主要言论吗?
答:可以的。我这回发言,一共有四次。第一次在大会期间的小组会上,后三次在政协直属组我所作的答辩及补充,内容有重复,也涉及其他问题,但中心是人治和法治。
1978年2月15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期间,我在小组会上说:“现在我们又有机会讨论宪法,参与制定宪法了,这是一桩可喜的事情。在旧中国,从民国元年开始,便有过各种临时的、正式的宪法;新中国成立后,有过1954年制定的新宪法。这些历史,我都经历过了。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回溯宪法的产生,最早起于英国,其来头是为着限制王权。因为王权无限大,一个人主宰一切,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使更多的人参与治理国家,便有了立宪之举。有了宪法,王权就受到限制,大家都要共同遵守的是宪法,宪法是最高的权威。”
“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有了自己的宪法,但宪法是否成了最高的权威,人人都得遵守呢?从三十年中的几个主要时期看,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样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不是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
“毛主席的这种稿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自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
“但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即便有人想搞人治,困难将会更大;再说经过种种实践,特别是‘文革’十年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迫切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十二分的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由人治渐入了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的所在,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我的这篇发言,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思如实地说出来,没有料到立即遭到反对,并在政协大会结束后组织对我进行批判,我奉命每次都出席,由这年三月开到六七月。
问:梁先生,当时主要批判您的哪些论点呢?
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大家的批判并不是针对我所说的事实说话,而是引申我的话头,概括几个问题,十分勉强地上纲上线,狠批我的“态度”和“用心”,如此而已!
比如,说我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毛主席的功过是非作出评价;说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当时上边还是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说我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我一贯反对阶级斗争学说,骨子里仇恨“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我诬蔑以“英明领袖华主席”(当时语)为首的党中央,是因为我说了一些当时还没有人说或不许说的话。诸如此类,我对这些,一般不作答复。
问:那么在这一次历时三个月的批判中,梁先生就没有再发言了吗?
答:那倒也不是。在五月间,我曾有过三次发言,都是在小组召集人要我表态时说的,内容没有新的,都是对我2月15日大会期间小组会发言的补充和发挥。
问:梁先生,您的申辩证明您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这在当时,您这种态度是会继续招来麻烦的。后来如何,梁先生可否谈一谈?
答:我五月间补充讲了这些话,六月间又开了几次批判会,但他们要说的话还是那些。大家都有点乏味,批判的火力一次比一次减弱。后来天热了,放暑假,大家在家休息。这年秋后恢复学习,没有再提我的事。不多久,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所肤浅地思考过、议论过的几个问题,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讨论,并有了趋向于一致的看法。对我的批判,自然也就不再存在了。
人们称粉碎“四人帮”是第二次解放,或第二个春天,但一时间乍暖还寒,欢呼之后则又愁眉思索起来。真正的春天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始。从1979年至今,九年过去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九年。在我个人,虽已进入垂暮之年,但毕竟也赶上了这种好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