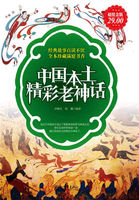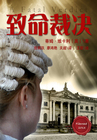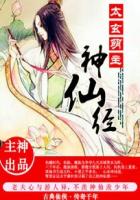不信?那就看看《东京梦华录》原文——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子(阁门),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
脚店(小酒店),“……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
“诸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
“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
东京汴梁,酒店之间竞争激烈,为吸引顾客,它们很注重推销、促销等。酒店门口高挂彩旗,旗上标着“新酒”二字(宋人以“新酒”为好,现在陈酒受捧)。宣和年间,丰乐楼重新开业,就有“金旗”相赏。
这次改建的丰乐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过一两夜则已。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
丰乐楼?大家也许不很熟悉,但要说丰乐楼就是《水浒传》里的樊楼,也就妇孺皆知了。
“白礬楼,后改为丰乐楼。”这是《东京梦华录》上的记载,因“礬”、“矾”相通,在通俗化的过程中,白礬楼成为白矾楼、矾楼。而有的笔记或演义,去掉“礬”下的“石”字,叫了樊楼。
在徽宗“商业政治化”,服务于皇家意志后,“白礬楼”则被皇帝改名为象征国家繁荣富强的“丰乐楼”了。
不管怎么改,丰乐楼都是李师师“坐台”的酒楼,丰乐楼都是市场化的产物——它所在的街道因经营白矾(礬)驰名东京,酒楼起先就叫白礬楼。
不管怎么改,丰乐楼都是千年不死的中国第一商业品牌——在今日开封,它还原为龙亭湖畔的礬楼;在今日杭州,它演化为西湖之滨的楼外楼。
据《西湖游览志》记载:“涌金门,旧名丰豫门。宋时有丰乐楼,与门相值,若屏障然。盖堪舆家以此当山水之冲,今移稍北,近柳洲寺。”
关于为何要在西湖之滨重建丰乐楼,张岱的《西湖梦录》上说:“高宗移汴民居杭地嘉(兴)湖(州)诸郡,时岁丰稔,建此楼,以与民同乐,故名(丰乐楼)。”
丰乐楼从东京汴梁走到行都杭州,说“建”的话,倒不如说“迁徙”更确切。
“连妓女都从东京汴梁迁到行都杭州了,还剩下什么没迁呢?还有什么没跟着高宗来呢?”杭州出版社副总编辑、南宋史研究专家徐吉军说。
西湖之滨的“虚拟东京”
临安丰乐楼遗址在今日西湖东南涌金池畔。
站在这儿,北望西湖,建于孤山的楼外楼、西泠印社等尽收眼底。
吴越国的时候,这儿建有城的西门,名叫涌金门。南宋一代,这儿还是西城门,不过名字改为丰豫门。
作为河南人,看到这样的名字,就会自觉不自觉地与河南的简称“豫”联系起来。但就此只说赵构怀念家乡什么的,就会和张岱犯下同样的错误。
张岱是大学者,但他毕竟是明代杭州人。
张岱把高宗命名新建的酒楼“丰乐楼”,解读为“高宗移汴民居杭地嘉(兴)湖(州)诸郡,时岁丰稔,建此楼,以与民同乐,故名”。这虽然道出了高宗不忘与他的东京老乡“汴民”同忧共乐的心态,殊不知,他最没法忘掉的还是老爹徽宗的“丰亨豫大理论”与代表东京一派繁华的旗帜——丰乐楼。
“丰亨豫大”是蔡京迎合、鼓噪徽宗的说法。
蔡京认为徽宗当政,“天下太平,府库充盈,百姓鼓腹讴歌,此所谓丰也,三代乌有此盛。既然丰亨,便可豫大”。并就此鼓动徽宗铸九鼎,做明堂,延福宫,筑艮岳,彰显盛德皇恩。
“丰亨豫大”之说把累朝积蓄一扫而空,徽宗自己也落了个北狩的下场。
但南宋初年,在反思靖康之败时,虽然诛杀了“宣和六贼”,但还是没谁敢把责任推在徽宗身上。
“丰亨豫大”之说虽起于蔡京,但已成徽宗理论。这,就不容怀疑徽宗误国乃至“丰亨豫大”之说了。
所以,找来找去,王安石成为靖康之败的替罪羊——都是王安石变法扰乱朝纲,把大宋给毁了。
既然不是徽宗的错,他的“丰亨豫大”理论(金钱物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扩大经济幅度,则会宽裕安逸,万物彼此都有循环性)就要再度高举下去的。
临安城的西门改称丰豫门,是一种继承;北门叫做艮山门,也是一种继承。
赵构知道,把北门称作“艮岳门”,是不怎么合适的。
整个东南地区,没有哪座山敢称为岳。他能凭空在一个没山的艮位,搞出个艮山门来,也算不辜负老爸对艮岳的一片痴心了。
丰乐楼是徽宗在京师汴梁实施“丰亨豫大”理论的大手笔。他自己玩了艮岳,当然也该让臣民有个喝酒快乐的地方,这也是把“丰亨豫大”理论落到实处的具体举措(“丰亨豫大”理论就纯理论而言,无可指责,那个时代能有这等高级理论,环顾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没谁敢与之争锋,而造艮岳等的行政错误,埋葬了“丰亨豫大”理论,是个大败局)。
既然追随赵构到杭州、嘉兴、湖州的东京老乡喜获丰收,又有了好日子,临安城新建的大酒楼被赵构命名为丰乐楼,既可聊表不忘汴京,也可聊作“中兴”的一个标志,多好呀!
不能忘却丰乐楼的,也不止他赵构一人。
诗人刘子翚当时所作《汴京记事诗》,就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诗——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礬楼。”
也许刘子翚压根儿就不喜欢丰乐楼这官方色彩太浓烈的名字,也许是诗歌本体的具体要求,他选取通俗化、百姓化的“礬楼”概念作为怀念对象。
他不仅怀念礬楼,还念叨着礬楼里的李师师和宋徽宗——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这么老的妓女都南迁了,还有什么留在汴京呢?
“整体搬迁,比上世纪50年代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入郑州,要彻底决绝得多!”河南大学程民生教授说,“东京虽然就此名存实亡,但在精神上,它依然镇服着杭州。在东京辉煌的光圈下,杭州始终不敢与东京平起平坐。”
“东京城虽然被金人占领,但灵魂不死,国家的首都,仍然是东京汴梁,而不是什么杭州。杭州只是皇帝临时驻跸的地方,公私文献中都称它是‘行在所’、‘行在’,顶多说个‘行都’。这是政治原则,也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东京的存在,是南宋的精神支柱,它能维系朝野上下和北方汉人。这面旗帜插在汴梁,却飘扬在南宋人的心中。”程民生教授说。
也因此,没有哪个朝代的迁都,像大宋这样,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将旧都独特的社会文明整体复制到新都,全盘“汴化”。
全盘“汴化”,构建了一个虚拟的汴京。恍惚下,他们还真的以为临安就是汴京——“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在虚拟的汴京,在汴京气象中,南宋人又过上“丰亨豫大”的奢侈生活,依然如在东京一样醉生梦死。“西施效颦”之全盘“汴化”
“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
这是《梦粱录》上的话。
一部《东京梦华录》,写的都是东京的生活,名副其实;一部《梦粱录》,写的尽是当时杭州的事物,却名实不副。
“在成为行都之前,杭州与东京相比,远远瞠乎其后,不敢与其同日而语。在东京过惯都城奢侈生活的人,突然避难杭州,一种失落感便油然而生。”徐吉军说,“袁褧的《枫窗小牍》,就写了发泄这种情绪的一段话:‘汴中(汴梁)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及余邸寓(住在杭州),山中深谷,杭田林莽塞目……唯野葱、苦荬、红米作炊;炊汁许许,代脂供饮。不谓地上天宫,有如此享受也!’”
唐代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何日更重游”,宋代柳永“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与苏东坡“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等——这些浪漫主义者的伟大作品,显然把更注重生活实质内容的人给忽悠了。
想想白居易、苏东坡在西湖筑下堤坝,杭州城市水利基本建设才刚刚开始。这些东西在中原地区大概两千年前就完成了,那时杭州能好到哪儿呢?
南渡之后,临安城几乎成为东京市民、中原侨民的天下,北方人口“数倍土著”。
先前杭州的一切,都不适合行都的要求。彻底“汴化”,在所难免。
在东京先进文化的冲击下,杭州土著甚至不知所措,以致在吃法、穿法上,都模仿东京人,闹出笑话:“东京人吃笼饼、蒸饼有去皮的习惯,这皆为汴梁风尘所致。但原来的临安居民,也依样画葫芦。妇女在街上行走,要方幅罗巾盖头遮盖半身。贵人出游,要一二十人手持镀金罐子,前导洒路过车,叫水路。这些皆因北方风尘,设而成习。临安的气候,显然和东京不同。但临安土著居民中的贵族妇女与士大夫出游,照样以方幅罗巾盖身、前面用水洒路,又成为后人的一大笑料。”徐吉军说。
临安的酒楼、茶肆和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他们把中原传统的烹饪技术、汴京风味、管理方法等,也带到临安,从而使临安一派“汴京气象”:“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也。”“今临安所货节物,皆用东都遗风,各色自若……”
赵构对此,也在点头称是。
一日,高宗玩赏西湖,泊舟苏堤,品尝“宋嫂鱼羹”后龙颜大悦,赐银百文。消息传开,缙绅豪贵纷纷下顾,“宋嫂鱼羹”于是成为南宋的一个名菜。至今八百多年来,它还是今日楼外楼的黄金招牌菜。
楼外楼的另一个黄金招牌菜,就是“西湖醋鱼”。
“西湖醋鱼原来叫‘醋熘全鱼’,它源自咱东京汴梁的醋熘鲤鱼。鱼用醋糖调味去腥,源于北宋。在杭州,它发展为西湖醋鱼;在开封,它发展为鲤鱼焙面。”中国烹饪大师、开封黄家包子老店厨师长朱永敬先生说,“从整个杭帮菜看,南宋时期形成的南料北(汴)烹,都是它发展的家底、套路。”
楼外楼“西湖醋鱼”把根归结在宋五嫂身上,鲤鱼焙面则把根寻找到赵匡胤那儿。
“赵匡胤要吃活鱼,这下难坏了厨子。于是,他们想了个办法,给鱼盖了床被子。”开封黄家包子老店总经理黄勇军说,“厨子对皇帝说,鱼活着呀,它在睡觉。”
赵匡胤一高兴,鲤鱼焙面就成为名菜了。
当然,鲤鱼焙面的历史还没有一百年,这是个传说。
西湖醋鱼的历史也没有一百年,它是个后来的名字。
但这两个南北名菜的根,都在东京汴梁,则是为专家认同的。
如今,楼外楼已经发展成为杭州的一个餐饮、食品集团,一年收入数亿元。其中西湖之滨的楼外楼餐厅,黄金周一天的最高峰值收入达到过70万元。楼外楼餐厅规模并不比开封龙亭之畔的礬楼大,名气也不比咱开封的响亮,但人家的生意却火暴得很。
而礬楼,还在死去活来的边缘挣扎。
一切都是经济文化中心南迁惹的祸?
难道时至今天,礬楼这样的品牌还养不起,保不住,必须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