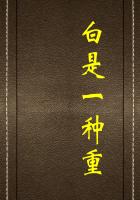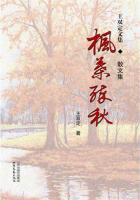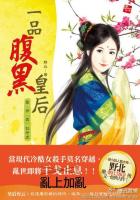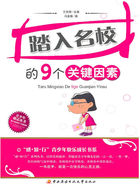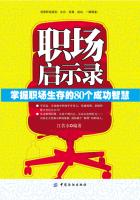我们试图去那个私人博物馆参观,好不容易找到了地方,却被告知瓷器已经转移到了别处。那一刻真的感觉特别遗憾,我们原本希望,那些瓷器能帮助我们感知八百多年前汴河的生动。
对于南去的中原移民来说,汴河肯定是异常生动的。
1127年前后,汴河送走了最后一批背井离乡的中原人,渐渐枯竭、死去。当恢复中原、还都开封的梦想越来越渺茫的时候,背井离乡的人回望家乡,他们心目中的汴河,应该永远都是美丽和繁华的。
亡国之悲和故园之思,在南宋成为最为重要的社会情绪。杭州繁荣起来了,不亚于当年的汴京,很多人安逸下来,恢复中原成了一个遥远的梦想。但在柔美旖旎的西子湖畔,还是有一些阳刚磊落的诗魂在怀念中原,他们内心积郁的悲愤,化为南宋文学最动人的光芒。
中原北望气如山
1125年10月,北宋官员陆宰被调任京西路转运副使(相当于河南省财政厅副厅长),他带着家小沿汴河北上开封。10月17日夜,静谧的汴河上响起新生儿响亮的啼哭,陆宰的第三个儿子降生在舟中。由于陆夫人前一天晚上梦到已故大文学家秦观(字少游),陆宰给这个儿子起名陆游,字务观。
陆家刚到开封不久,就遭遇金兵第一次围攻,饱受煎熬。在靖康元年金兵第二次围攻开封前,陆宰被免职,带着家眷到了安徽寿春,侥幸逃过了那一场大劫难。但1129年金兵再度南侵,陆家被追赶着仓皇南逃,年仅4岁的陆游,刚记事就品尝到了国家深重的苦难。北宋覆灭的耻辱,让陆游的父辈悲愤难抑,“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尽管金人凶悍强大,他们的言辞中也毫不畏惧。出生在这样的时代,感受着如此的家庭氛围,陆游从小就立下了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志向。
他的很多诗歌热情奔放,豪壮磊落: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终其一生,陆游期望恢复中原、洗雪国耻的热情都不曾减退,花开花落,长空雁叫都会激起他的满腔心事。直到去世的时候,陆游仍是死不瞑目,写下那首著名的绝笔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收复失地当然不只是陆游的呼喊。南宋初年,士大夫目睹中原失陷,山河破碎,创作风格发生巨大变化。北宋末年的留恋光景、清丽婉转,一变而为感怀世变、苍凉悲愤。表现对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成为文学的主题,这样的作品,使南宋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
实际上,南宋文学中,恢复中原、洗雪国耻的最强音,应该说是名将岳飞的诗词。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艮岳)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字里行间,张扬着一代名将的豪情和自信。
可惜岳飞留存下来的作品太少。他被残杀后,与他交往较多的人,都被视为“交通叛将”,曾做过他幕僚的文人,更是遭迫害的对象,身家性命都受到威胁。为了全身避祸,这些人大都将与岳飞有关的文字予以销毁。
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南侵。大兵压境之时,为岳飞平反昭雪的呼声日益高涨。岳飞旧部众口一词,“哭声雷震”,为岳飞申冤。但是宋高宗死不低头,仍不肯为岳飞彻底翻案。1162年,宋孝宗即位,为了鼓舞士气,才认真调查关于岳飞冤狱的情况,为岳飞平了反。这时距离岳飞之死已经二十年,别说关于岳飞的诗词,就是岳飞的尸骨都无处寻找,朝廷很是尴尬,只好以五百贯的高价购求岳飞遗体。这时候,一个感人的故事才大白于天下:岳飞遇害后,临安义士隗顺负尸越城,将其草草埋葬。为了便于以后识别,隗顺将岳飞随身佩带的玉环系于遗体腰下,坟前种植了两棵橘树。孝宗将岳飞“以礼改葬”,这才有了西子湖畔栖霞岭下的岳飞墓。
岳飞的不幸,似乎早早就昭示了南宋爱国志士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群体命运。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162年,南宋政坛又出了位文武全才的英雄。这位英雄以50名骑兵袭击5万金军大营,活捉叛将,号召旧部万人反正,然后长驱渡淮,押解叛将到建康(今南京)斩首。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此人名重一时,“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这个英雄的名字,叫辛弃疾。
辛弃疾出生于1140年,即岳飞在郾城被迫班师的那一年。他是山东历城(今济南)人,由于父亲早亡,他从小跟着祖父辛赞在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谯城区)长大。为家计所累,辛赞靖康年间未能脱身南下,后来虽然当了金国的谯县县令,却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他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精心培养这个从小不凡的孙儿。他曾两次令辛弃疾跟着手下的官员,到当时金人重地燕京,以“谛观形势”。辛弃疾从小目睹了女真人统治下汉人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立下了毕生努力以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
辛弃疾从小有才名,他跟着亳州名士刘瞻读书时,师门弟子众多,而最为出类拔萃的是辛弃疾和一个叫党怀英的人,两人才华相当,并称“辛党”。不过后来两个人却南辕北辙,党怀英在金贵显,辛弃疾走上抗金的道路。
1161年夏秋间,金主完颜亮大举入侵,北方沦陷区抗金武装蜂起。这时辛赞已去世,22岁的辛弃疾也在济南南部山区聚众两千人,投奔著名义军首领耿京。辛弃疾力劝耿京“决策南向”,与南宋朝廷正规军配合,共同抗击金兵。1162年正月,辛弃疾奉表归宋,接洽南投事宜。半个多月后,辛弃疾在北归途中获悉,叛将张安国杀害耿京投降了金人。怒发冲冠的辛弃疾率领跟随他的五十名骑兵直驱山东,袭击金军大营,将张安国劫出金营,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带领他们长驱渡淮,投奔了南宋。这一年,辛弃疾还不到23周岁。
在沦陷区的壮举,使辛弃疾名重一时。高宗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辛弃疾开始了在南宋的仕宦生涯。
初来南方,辛弃疾热情高涨,写下了不少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广为传诵,深受人们称赞,但以苟安东南为满足的朝廷却反应冷淡。
辛弃疾在南宋生活了四十多年,担任过多年“厅级干部”,如果混日子的话,生活可以过得相当不错。但辛弃疾也是一个岳飞那样喜欢找“不自在”的人,他希望的,是走上抗金前线,收复中原,为国立功。朝廷偃武修文,不思进取,辛弃疾满腔豪情,却不得不过着“宜醉宜游宜睡”、“管竹管山管水”的生活。
壮志难酬、无路请缨化为压抑不住的悲愤。辛弃疾只有“醉里挑灯看剑”,只有发牢骚:“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内心的悲凉和无奈在一首词中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辛弃疾如此痛苦,在于他能深切体会沦陷区百姓的苦难。看到这种苦难的,还有一个叫范成大的诗人。
1170年,宋孝宗决定派人去金国谈判,废除南宋大臣代表皇帝跪受金人国书的耻辱性礼仪。大臣均畏惧不敢奉命,唯有范成大挺身而出,抱着必死的决心出使金国。他在金国几乎被害,但终于不辱使命,赢得双方朝野的一致称赞。在故都开封,亲身见闻使范成大写下了著名的《州桥》:“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南宋中期,辛弃疾、陆游、范成大这一批伟大的诗人相继去世。此后,就没有什么人像他们那样连做梦都盼着北伐中原了。悲愤激昂的格调不再为人崇尚,而没有了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南宋的文坛少了精气神儿,也就很少再出现大家和精品了。
在开封,北宋故宫遗址在龙亭湖水下十米,艮岳不见踪影;在杭州,南宋故宫遗址被掩遮在凤凰山的森林中,据说这凤凰山就是艮岳的“模特”——徽宗照凤凰山的葫芦画了个艮岳的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