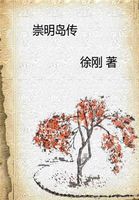(“一个吃饭样子难看的人,是不会幸福的。”我一直记住母亲的这句话。)大碗死了很多年了,他四十六岁的儿子(又是一个单身)前年死于溺水。我想,村里没有人会想起他。
吞咽……我不忍说出与它有关的人与生活。
【瓦屋顶】:南方,以雨滴的速度奔跑的南方,一片黑色的屋顶让人伤感。黑色的、延绵的、孤立的、长条形的。屋顶。它是降落在房子上的天空布景。
昨天,我整理书房的时候,看见一张旧照片—一块一块的屋顶,交错有致,灰白的院墙斑驳。瓦垄是一条时间的地下河,明亮而幽深。瓦,一片压着一片,像闪闪发光的鱼鳞。我突然想起我光着上身劳作的祖父,雨水打在他身上,溜溜地下滑,一点雨迹都没有。他油亮的,瓦釉色的身子。
时间一样古老的南方,一个旅人走在乡间小道上,瓦屋顶让他热泪盈眶。
【院】:一扇竹丝编的院门,在风中日夜拍打。
编竹丝的老人,皮肤松榻,光秃的牙床被寂寞的岁月呜呜吹响,空空的,一把缺了口的蔑刀红锈斑斑。他已死了多年,他出生的旧屋只留下颓圮的断墙。
狗尾巴草在墙头摇曳生姿,许多秋天中的一个,风声从墙的牙缝中冒出。
墙已没有泥,嶙峋的石块黏连一副壮实的身子。像编竹丝的老人,浑身只剩下坚硬的骨头。
在院子里,竹丝从他指尖滑过。而谁能看见他的躯体像一座庙宇,黑暗、神秘、诡谲?
枯黄的瓜藤,废弃的草料,散落的木屑。一座院子就像扔满皮壳的果盘。我要放下所有的事情,悉心去清扫、收拾、整理。这样的一天,是怀旧和爽朗的,适合一个人在缅想中俯身细小的事物。一天中,我所遇见的,将逐样逐件归类,曾经生长的必将消亡,不消亡的必将不再生长。
我还要为几株果树的幼苗松土、浇水、培根,我不想它像我一样在穷瘠的硬土里挣扎。
我推开院门,看见一个挽髻的老妪坐在竹椅上,脚边摆一个圆笸。
“奶奶!”我脱口而出,没有回应。
原来是昨日烧剩的一堆灰烬。我顿时弥眼泪水。祖母常常坐在院子里,为穿烂了的布鞋打底掌帮。圆笸是竹青丝编的,手工精细、图案素美,在阳光下,弥散桐油的清香。那时我还是孩童,整天紧跟着祖母。多年后的一个初冬,祖母坐在院子里取暖,打瞌睡,再也没有醒来。
地上重叠的脚印,被又一年的春雨洗刷。
我在枣树下,透明的清晨在舌尖上激荡,米碎的枣花落满双肩。花在消失,果实日益圆润。黑翅白肚的石灰鸟啁啾着,从一枝跃向另一枝,妙趣的夏天开始。院子宛如一把打开的折扇。
我们将穿过旷野与河流,春夏秋冬也穿越我们,在躯体里重复。而所有的路又折回院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斑驳的脚印也被淤上一层污泥。
星空肖像
时光夹裹着无际的黑暗而来,缓慢而磅礴,深深塌在祖父的脸上。这是祖父的另一种沦陷。他脸上堆叠着时间的皱褶,呈波浪形,覆盖了他灰白色的记忆。他明白,人生终究是一次单程旅行,路上众人喧哗,而最终的旅程是孤身一人。他躺在厢房的平头床上,睁起凹陷的眼睛,看着黑褐色的瓦垄。祖父已经卧床两年,背上长出了褥疮。厢房光线黯淡,一扇木格窗对着一片田园,馥郁青葱的植物气息浮在空气中,被一阵微风带进祖父虚弱的鼻息。这时,祖父会对我说,你扶我到后院去坐坐。
后院有两棵枣树,一棵柚子树,有两排瓜架搭在矮墙上。南墙是南瓜架,北墙是黄瓜架,初夏时节,肥厚宽大的南瓜叶和细长粉黄的黄瓜花,给院子增添了闹意,与院子毗邻的是禾苗涟涟的田园。祖父坐在枣树下,有了复苏的感觉。枣花粉细地白,压在树丫上,一层叠着一层,像一顶编织的花冠。每天傍晚,祖父都会在后院里小坐。晚霞褪去了绯红,化为一片缠绕飘忽的白云,不远处的山峦青黛如眉,天空澄蓝如洗,爆出三两颗星星。祖父的衰老是从两条腿开始的。他是箩筐腿,过了八十岁,双腿已经不能承受身体的重量。他说,人的衰老就像一栋倒塌的旧房子,屋漏一阵子,墙颓败了,柱子坍塌,荒草从厅堂里长了出来,整个儿成了一片圮墟。
是的,祖父平静地迎接(而不是屈从)自己身体的坍塌,在卧床的两年时间里,他从不呻吟,也从不抱怨。他慢慢等待沉寂时刻的到来(像厚重泥土的覆盖)。有几次,祖父一个人在厢房里,突然爆出一句质问:“你是谁,为什么站在我的床前?”我听到质问声,连忙跨进厢房,只见灰尘在木格窗的光线里悬浮,密密的,闪着恍恍惚惚的光泽。祖父说,刚刚有一个穿黑衣的人站在床前,高高大大,手上拿着桃木手杖,不说话,咧嘴笑着。我说,那是你的幻觉,我们村里没有拿桃木手杖的人。这让我惊惧而诧异。祖父说:“噢,你去拿酒来,我想喝一口酒,我好几天都没喝了。”我说,你早餐还喝了小半碗呢。
烧酒、麻子馃、肥肉、辣椒,是祖父一生的挚爱。麻子馃,我吃不了三个,他却能吃一大盘。一块巴掌大的炖肉,两口吃完。他的嘴巴把肉包住,一口咬下去,肥油从嘴角两边“扑哧”溅出来,他用手抹一下嘴,说,烧酒、肥肉、老婆,是三件宝啊。在后山的菜地,他种满了朝天椒。我吃朝天椒,嘴唇都辣肿起来,祖父却一口一个。新谷归仓了,他选上好的谷料挑到酒坊里,对酿酒的师傅老四说,出酒的时候叫上我啊。
打开后院的柴扉,拐过两条田埂,弯过一个荒冢,就到了酒坊。酒坊围在一座宅院里,乌黑黑的苍蝇在宅院的上空“嘤嘤嗡嗡”,酒糟的香气四散。出酒的那天,祖父肩扛一个大酒缸,我手提两个大锡壶,早早到了酒坊。锡壶是装头酒和尾酒的。我坐在石灶前,负责添火。大铁锅上罩着一个两米多高的木甑,木甑上压着一口盛满水的铝盆。一根细长中空的竹管从木甑顶端的切口上,连接到酒缸。祖父端来小圆桌,摆上腌辣椒、酱蒜头、南瓜干等小菜,坐在酒缸边,喝一口酒,摇一下头,说,辣口,辣口,这样的酒喝下去,再辣的太阳也扛得了。蒸汽弥漫了整个酒坊,酒香引来四邻的酒客,小桌围满了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灶墩上,品着刚出炉的热酒。祖父酒量大,很少醉。假如他说话有些结舌了,脸色酱红,不时地摸自己光光的脑门,手势略显夸张,他已经微醺了。
矮小、强壮,宽厚的脊背像一堵墙。这是我年幼时记忆中的祖父。吃过午饭,祖父端一条板凳坐在屋檐下,叫我:“给我刺刺水泡。”每到夏天,他的脊背上冒出密密麻麻的酒疹。酒疹有一个个细小的水泡,水泡破裂,疹水流过的皮肤会在第二天冒出珠泡。我用酒在他的背上抹一遍,再用竹签把珠泡剔破。酒疹溃烂,有腥臭味。但我不怕,刺水泡仿佛是我的一种乐趣。我并不知道,祖父终身都被酒疹所折磨。他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是打赤膊的,穿一条宽大湛青色短裤,光着脚,腰上别着一个油亮亮的布烟袋。他坐在板凳上,躬起身子,像一面牛皮鼓—我认识了男人的身体,饱满如牛,壮实如泥,浑身有瓷缸的釉色。
一个死人,三十二年后,仍然冰凉在我的记忆里。他是我的邻居和尚老爷。他七十多岁,自然死亡。我母亲说,和尚老爷死了,我带你去拜拜,他会保佑你的。那年我六岁。我拽着母亲的衣角,推开邻居厚重高大的木门,看见门后的躺椅上盖着一块白布。母亲把白布掀开,露出一张七十多岁的男性脸孔,或许是光线阴暗的缘故,脸孔发黑、颧骨峻峭、嘴巴张开、露出不规则的牙齿。我吓得号啕大哭,夺门而逃,恐惧的记忆具有一种压迫感。
我不知道这种压迫感是否与生俱来。祖父卧床的那年秋天,祖母仙逝,享年八十六岁。其实祖父过了八十岁,就不能下地了,而祖母还是异样的强悍。祖母和祖父同庚,比祖父早一天出生。我的三姑离我家有五里路,八十岁的祖母还能一个上午走一个来回。她挎一个竹篮,提着时鲜菜蔬,颠着三个手指宽的小脚,沿山边羊肠小道,给三姑送菜去了。有一次,到了日落时分,祖母被邻村的石匠师傅送回家。祖母说,她走到夏家墓的十字路口,走错了岔道,迷路了。邻居冬瓜婆婆一次路过我家门口,对我说,别看你祖母身体好,可能你祖母先你祖父而去。我有些不高兴,对活着的人议论死期是极不恭敬的。冬瓜婆婆脸上长满皮癣,有一块块的花斑白,她说,你祖母的后脑门都竖起来了,你祖父腿脚虽不灵便,但脑壳像个南瓜,浑圆的。
坐在高脚凳上的祖父有点像个孩子。每到吃饭,他会说,今天怎么没客人呢。有客人,就有人陪他喝酒了。客人来了,他坐在上座,拉开架势,吆喝我:“把酒拿上来,我要开开酒戒。”其实他每餐都喝,谁都劝不住。他说,酒都不能喝,还做人干嘛。我祖母就骂他,一个老不死的老头,饭都盛不了,喝起酒来有使不完的劲。祖父是个乐观的人,即使下不了地,也还是清清爽爽的,他说,你别看我箩筐腿,我一辈子走了三辈子的路,你看看,这栋房子的木料,哪一根不是我从高浆岭扛来的,一个晚上要走八十里山路,走了整整三年。祖母却不一样,神志有些迷糊,自己家的菜地也找不到,换下来的鞋子也不知道扔哪儿了。她有一个小菜橱,有好菜,她就盛一碗,放在小橱里,备用吃。她从来忘记吃,等她端出来吃,已经是个空碗。我母亲把菜倒了,菜早已霉变,引来绿头苍蝇,“嗡嗡翁”,吵死人。
后院的枣树下,祖母坐在笸箩边,把旧鞋底拆下来,用米糊一层层地粘上布料,又一针针地纳起来。祖父坐在她边上晒太阳。隔一会儿,祖父喊一声:“荷荣,荷荣。”我祖母应一声:“老头子啊。”一个叫着,一个应着,但彼此都没有别的话说。柚子花开的时候,整个院子有一种黏稠的青涩香味,给人潮湿温润的感觉。矮墙的瓜架一天天抽出丝蔓,撑开毛茸茸的瓜叶。一地的枣花如蓝花布上斑斓的图案。
1993年的秋天,是一个特别暖和的秋天。地气上抽,田地金黄。干燥的泥土很容易让人长夜瞌睡,山峦下的村舍寂寂。祖母在酣睡中再也没有醒来。祖母面容慈祥,像一块被雨水冲刷多年的瓦,纹理细密,手摸过去,有时间的质感。她的眼角有浑浊白色的液体,这是她每到秋天就有的。每到秋天,祖父端一把锄头,提一个竹篮,到山涧边,挖一些金钱草、蛤蟆草,晒干,熬汤给祖母喝。
死亡变得不像我恐惧中的那般可怕—一个拒绝聆听和观看世界的人,不会介入喧哗。祖父睡在另一个房间,他静静地听着我们干涸的痛哭,只有在沉睡的时候,他不断地叫:“荷荣,荷荣。”声音低沉,像一股岩浆埋在废弃的井里。十多年之后,我仍然能听到这个声音,从井盖的裂缝里突然冒出来,荡然回响。祖母的房间一直空在那儿,麻丝的蚊帐泛着淡黄色,草席还留有熟睡人的体温。祖父有时候整个下午坐在床沿上,仿佛他在等着熟睡的人醒来。他用手摸摸草席,摸摸枕头,拍拍被子上的灰尘,把半暗的窗子完全打开,从衣柜里翻出祖母的鞋子摆在床前。仿佛这是一天的早晨,他们穿衣下床,开始一天的生活。仿佛他们一生经历的事情,又重新开始。
溽热的夏天,南方的空气会冒出“噼噼啪啪”的火花。三哥背着祖父去饶北河洗澡。菟丝子缠绕着柳树,西瓜地上的茅棚在旷野里显得孤零零。饶北河在村口形成半月形的河湾,洋槐像瀑布一样,翻卷着向上喷涌。祖父的手臂干枯如藤条一般,搭在三哥的肩膀上,脚细瘦,弯曲,略有变形。祖父的身体,在那漫长的岁月里,都涨满潮水,汹涌着力量,现在潮水已经完全退却,露出石头嶙峋的河床。他甚至说话都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祖父曾经是村里最好的水手。饶北河暴涨的季节,上游冲下来浮木,他跳进水里,把浮木捞上来。他打个赤膊,泥礅一样壮实,阔大的脚板打在地上,有“噗哒噗哒”的声音,大腿上的肌肉一坨一坨地晃动,晃动得那样有节奏。他扛着浮木,竖直的腰板就是我记忆中的墙。根根浮木都可以做房梁,一个雨季,我家的后院堆满了木头。
坐在埠头的石礅上,祖父像一团晒干的麻子馃。他胸脯上、腹部上,原有的硕大肌腱像水渗进沙子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黝黑的一层皮耷拉下来。他背部酒疹留下的白色斑点,呈卤花的形状,一小朵一小朵,缀连着。祖父说,老四(我三哥),你明天早上叫难民来,给我剃一个头。难民是个剃头师傅,每月的十五那天,他都要给我祖父剃头,这个习惯保持了二十多年。其实,我祖父在七十来岁的时候,头发全掉光了。剃头的时候,难民扎起马步,脖子上搭一条破布一样的蓝色毛巾,流着稀稀的鼻涕,用剃刀细心地刮祖父头上稀疏的绒毛。老四说,我明天会准备两个好菜,拎到夏家墓的。我们把祖母一个人扔在夏家墓的荒冈上。
看上去他像一只抽空的气球,干瘪,皱皱地扁着。他的阳具紧缩在胯裆里,看起来和一只田螺没有区别。我给他穿衣服的时候,他还略有羞涩。他说,我给你穿衣服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一晃眼二十多年了,怎么就像昨天一样。他又说,你该结婚了,我想看看你小孩是不是和你一样站在灶台上往锅里拉尿。我说,会的,有适合的就结婚。他笑了起来,露出空空的牙床。他说,结婚就是搭伙烧饭,不要彼此计较。我想起小时候,我和他一起上厕所,射尿比赛,看谁尿射得更远。他把尿射过梁上,“嘟嘟嘟”,把猪淋得浑身尿骚。现在他每次拉尿都要我扶着,他一手撑着墙,一手掏进裤裆,掏了好久什么也掏不出来。他的尿从那个田螺壳里滴出来,一滴,一滴,不成线,像阵雨后的瓦檐水。有一天,我祖父对我说,你把酒缸搬到你父亲房间去吧。我说,这个酒缸在你身边有五十多年了,还是放在你这儿吧。祖父说,酒一点味儿都没有,倒像一把刀子,割人。我把手按在祖父的上腹部,说,你可能胃受寒了。他戒酒没几天,整个人完全失去了知觉。他躺在床上,瘪着嘴巴,眼睛蒙上一层灰白色的翳,额头冰凉。我们叫他,他喉结蠕动,好像他的声音从千里迢迢赶来,汇聚在喉管里,再也走不了,彼此扭结,形成洪流,却冲不出那道闸门,被堵着。他厚重的眼睑包裹着一个旷阔邈远的星空,星光细雨般撒落。瓦蓝深邃的星空,他反反复复地梦见它,他变得越来越轻,一缕光一般与整个苍穹融为一体。
我的女儿骢骢今年七岁,像蟑螂一样害怕炎热的太阳,她不知道饶北河有多宽。或许她无需知道,夏家墓矮小的荒冈上,是我记忆的源头。那是我庞大家族最高的山峰。山冈有常年油绿绿的山茶树,荒草遍野,苦竹和巴茅被风吹动的时候,有“呜呜呜”的声响。我有多年没去哪儿,仿佛它与我的生活无关。我的父亲今年七十三岁了,戴着一副假牙,头上稀疏的毛发沦为配角,即使他一个人吃饭他也把持着上座,一餐半碗烧酒,吃很咸很辣的菜。很小的时候,我畏惧的一件事情,是祖父离我们而去。一家十三口的吃喝,都是祖父一人操持的,开荒种地,我们怎么吃也吃不完。父亲则是一介书生,除了会写毛笔字,造造账册,什么事情也不会做。衰老犹如黄昏,在日落时分准时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