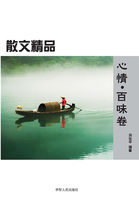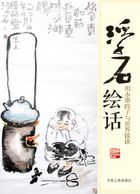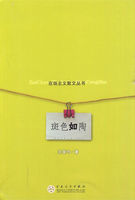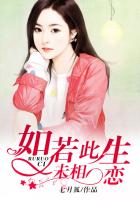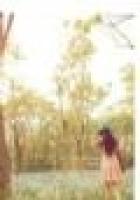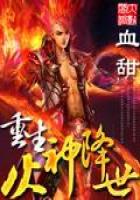至于超乎修辞或技法之上的,则有题旨上的比附。在《荔枝蜜》中,因小时候被蜂叮过,本是不大喜欢的,但经过一番教育,懂得蜜蜂的生活及劳动后,便改变了认识。“我的心不禁一颤: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行文到此,有这样的赞美,本是文意已足。但作者往往写了物事,还要写人事,因而下文还有一段写农民的劳动。这样写不是为了落实,正是为了比附。至于结尾,又不无蛇足。即作者态度上不只是要向蜜蜂学习,甚而还在梦里变成了一只小蜜蜂。古代笔记小说中的物,千方百计都向往着修炼为人,作者在这里则想着物化了。其实就是向蜜蜂学习,也没必要让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或者说要变也当变成一只老蜜蜂。不用说,文中的感情够强烈的,但理太浅,因而显得不相称。若是理性方面也能增加力度,方能情理相生。或许这里尚有那年头思想意识决定态度的影响,要说转变也真够快的。此外像《秋风萧瑟》中写长城,写历史的感喟,然后归结为“换了人间”,则主题明显是借来的,可以无需多说。
比附作为一种修辞或技法,本身并无优劣可言,关键在于运用。杨朔大量使用比附,其不当之处或许就是过于升华了。如《蓬莱仙境》是写新旧社会里翻天覆地的变化,文中多有写实的人事及场景,本当自有表现的意义。但文末由小外甥女的绣花升华为全国人民用大地当素绢,正是要共同绣出一幅伟大的杰作来,则又是让小事情搭上了大道理。作者的故乡是一个有蓬莱仙境的地方,但所触及的社会生活及写作心态也不无“蓬莱仙境”的。此无它,就在于升华中融入了太多诗意的因素。同样的写法也见于《海市》:“如果你到我的故乡蓬莱去看海市蜃楼,时令不巧,看不见也不必失望,我倒劝你去看看这真实的海市,比起那缥缈的幻景还要新奇,还要有意思得多呢。”构思之巧,在于把虚幻的海市搬到现实中来,用以突出现实的巨变。就其所处的时代而言,唱赞歌本来也很正常,但散文中还要有切实的一面,这样二者便无法协调起来。小中所见之大毕竟有限,若一味升华,则真实的也会虚幻起来,又变成海市了。
再看《茶花赋》,先写了茶花的美,再转为称赞育花的人,结尾则以画一幅画来象征祖国的面貌。这就是杨朔散文写作的三部曲,颇有代表性。往往先写景物,再配以人事,然后由二者比附出一个大主题来。甚而,《泰山极顶》一文中本来并没有看到日出,但作者仍要虚拟出一轮红日来。由实入虚,是作者惯用的手法,不少篇章都是这样安排的。所谓卒章显其志,但其志在大,就得拔高主题,且不管文中写的多是小事情。即便是小花小草之类,仍要映出红太阳的光辉。此种比附,当然是过于虚了,或者说过于写意了。杨朔自谓把散文当成诗来写,或许就是为了文中便于抒情。但此种诗意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美化,既美化了生活,也美化了感情。同当时的许多作者一样,杨朔散文写作也是从通讯起步的,其长处在于写实。就写实而言,则要不避其小,比如孙犁的一些散文就是这样。由通讯而散文,好处在于延续了写实,但要有文学的意味,则需进一步写意。由写实到写意,杨朔的做法就是诗化,且大力抒情,从而唱起赞歌来。本来写实的笔墨自有魅力,即留下一些生活的印迹,但作者就是念念不忘要比附上一个大主题。杨朔的散文形成了模式,从修辞技法到篇章结构再到题意主旨,往往都出于一种比附。从这里,还可见出写作思维上的趋同。
(原载于《写作》2007年5月)
写人与写己
小说的人物形象中,有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之说。扁形人物着重展现的是人物性格的一些侧面,圆形人物则要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还包括性格的形成过程。散文中的人物,大多也是扁形的,即着重表现一些性格的要素。但正如鲁迅所赞许的画眼睛的白描手法,着墨不多,也可形神兼备。这里以汪曾祺的《闹市闲民》为例,说一说写人的散文。
《闹市闲民》写的是一个相识的老头。老头独自住在一间屋里。“屋里陈设非常简单(除了大冬天,他的门总是开着),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杌凳,三个马扎儿,一张床,一目了然。”这“简单”是文中的关键词,可以用来概括老头的生活。接着写老人的相貌,突出了眼睛。“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养目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混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笑意表明待人接物的和善,而天真则是性情的流露。换言之,即性格中尚有一种天真。老人原来是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但他不愿跟老伴及儿孙住在一起,说是乱,这表明他的生活习性,仍旧是保持一种简单。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条,或是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坐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拨的鱼儿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拨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搅搅。’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的面总是一个味儿!浇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时,切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儿’。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他不大喝水),涮涮碗,坐在门前的马扎儿上,抱着膝盖看街。”这是文中一个主体段落,讲老头的生活,仍可以概括为“简单”二字。但作者特地写到拨鱼儿,则流露出一种对技艺的欣赏。就做菜而言,汪曾祺也是好手,但各有所长,即做不来那拨鱼儿。这说明就是简单中,也自有一种精致。老头吃过了饭,就看街,让生活保持一种平静。“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
汪曾祺在《散文应是精品》中说:“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有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即使是写游记,写习俗,乃至写草木虫鱼,也都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汪曾祺说小说家写散文的特点是文中有人,即有如小说中那样的人物。不过即便文中没有具体的人,也还有一个自我。自我,就是散文中所写之人。凡所抒写,都通过这个自我来感受,从而有所取舍。《闹市闲民》中是有人的,那么人物与自我也就应当有所关联或沟通。不过此种关联或沟通,不等于在人物与自我间画等号,那是不可能的。比如同是讲吃,汪曾祺就无法如此简单,因而他的菜篮子里,种类要丰富得多。至于老头,再多的种类或花样,于他都不起诱惑,他仍然延续他那种简单而不无一点精致的生活。
不可将自我与笔下的人物等同起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笔下人物仍可反映自我的。换言之,写人也即程度不等地写着自己。自己的心性,最容易在情感及态度上流露出来。大体上说,有激赏的或反感的以至厌恶的,等等。不用说,汪曾祺对笔下的闹市闲民怀抱着一种赞赏的态度。众所周知,传统的人生曲线是亦儒亦道的,大致对应于人生的进取与恬退。就一个人的经历来说,年轻时不妨多一点进取,年老时则要以恬退为主。作者笔下的那个老头,显然是一种恬退人生。他的生活很简单,但善于把持自己。不仅不添乱,还能用天真的表情打量着街头闹市。也正为此,作者才赞许老头为一个活庄子。
关于写文章,古来有文如其人的说法,但也引来颇多争议。余光中在《为人作序》中说:“我不认为‘文如其人’的‘人’仅指作者的体态谈吐予人的外在印象。若仅指此,则不少作者其实‘文非其人’。所谓‘人’,更应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自我,此一‘另己’甚或‘真己’往往和外在的‘貌己’大异其趣,甚或相反。其实以作家而言,其人的真己倒是他内心渴望扮演的角色:这种渴望在现实生活中每受压抑,但是在想象中,亦即作品中却得以体现,成为一位作家的‘艺术人格’。”这种艺术人格的提出,才不会与其人等同起来。就这个意义上说,汪曾祺笔下的那个闹市闲民,也可视为作者的一个理想人格。
(原载于《写作》2008年6月)
幽默及反讽的笔调
王小波的散文随笔,颇具幽默及反讽。比如《我看文化热》,文中先讲几次文化热的现象,然后再讲自己对文化的理解,表明一种反思。“我知道一种文化的定义是这样的:文化是一个社会里精神财富的积累,通过物质媒介(书籍、艺术品等等)传诸后世或向周围传播。根据这种观点,文化是创造性劳动的成果。现在正热着的观点却说,文化是种操守、是端正的态度;属伦理学范畴。”两相比较,只讲伦理或操守,无疑是缩小了文化的内涵。“不管怎么说,只有这么一种成果,文化显得单薄乏味。打个比方来说,文化好比是蔬菜,伦理道德是胡萝卜。说胡萝卜是蔬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让我们彻底没菜吃。所以,我希望别再热了。”这个通俗的比方不仅用得很贴切,还颇有反讽的意味。
再看《椰子树与平等》:“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插队。当地气候炎热,出产各种热带水果,就是没有椰子。整个云南都不长椰子,根据野史记载,这其中有个缘故。据说,在三国以前,云南到处都是椰子,树下住着幸福的少数民族。众所周知,椰子有很多用处,椰茸可以当饭吃,椰子油也可食用。椰子树叶里的纤维可以织粗糙的衣裙,椰子树干是木材。这种树木可以满足人的大部分需要,当地人也就不事农耕,过着悠闲的生活。忽一日,诸葛亮南征来到此地,他要教化当地人,让他们遵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干我们的活,穿我们的衣服,服从我们的制度。这件事起初不大成功,当地人没看出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优越之处。首先,秋收春种,活得很累,起码比摘椰子要累;其次,汉族人的衣着在当地也不适用。就以诸葛先生为例,那身道袍料子虽好,穿在身上除了捂汗和捂痱子,捂不出别的来;至于那顶道冠,既不遮阳,也不挡雨,只能招马蜂进去做窝。当地天热,摘两片椰树叶把羞处遮遮就可以了。至于汉朝的政治制度,对当地的少数民族来说,未免太过烦琐。诸葛先生磨破了嘴皮子,言必称孔孟,但也没人听。他不觉得自己的道理不对,却把账算在了椰子树身上:下了一道命令,一夜之间就把云南的椰树砍了个精光;免得这些蛮夷之人听不进圣贤的道理。没了这些树,他说话就有人听了--对此,我的解释是,诸葛亮他老人家南征,可不是一个人去的,还带了好多的兵,砍树用的刀斧也可以用来砍人,砍树这件事说明他手下的人手够用,刀斧也够用。当地人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怕了诸葛先生。我这种看法你尽可以不同意--我知道你会说,诸葛亮乃古之贤人,不会这样赤裸裸地用武力威胁别人;所以,我也不想坚持这种观点。”
本文由一则传说写起,叙述的是诸葛亮南征时砍了云南的椰子树。但不是在故事新编,而是展开评说。评说中,有阐释,有设想,但重在议论。至于作者为何要选择这则传说,也是有现实观感的,即插队的经历。传说中,诸葛亮南征时砍去云南的椰子树,为的是让当地人接受教化,但作者并不这么认为,而是引出一个平等的问题。“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就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铁棍一敲,一声惨叫,这就变过来了。”其实平等与不平等的问题,也应当辨证地看,才能分清何者可讲平等何者无法平等。比如作为公民,应当是平等的。至于知识方面的差异,却难以做到平等。作者的用意在于讽刺向下拉平的做法,即要么把聪明人打笨,要么就是傻人有理。本文所叙事例有其形象性,此为形象说理。但说理中还有一种谐趣,从而起到反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