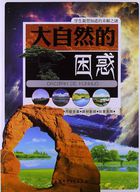孤独者
西里艾尔·皮思
濮佛尔的小屋子是孤立在莽原之中……涂着赭黄色的粉的,凸凹龟裂的四面小小的破墙;一个半坍的,在西边遮着一片幽暗的长春藤的,灰色的破屋顶;有青色的小扉板倒悬着的两扇小玻璃窗;一扇为青苔所蚀的苍青色的低低的门;便是我们在那凄凉而寂静的旷野中所见到的这所小屋子……在那无穷的高天的穹窿之下,这所耸立在那起伏于天涯的树林的辽远而幽暗的曲线上的小屋子,便格外显得渺小了。它在那儿耸立着,在一种异常忧郁的孤独之中,在那刮着平原的秋天的寒冷而灰色的大风之下。
那认识他或只听别人讲起过他的几个人,称他为“濮佛尔”。
没有一个人记得他的真姓名。他过着一种完全的隐遁生活,离开有人烟之处有十二英里,离最近的村子有十六英里。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他和他的父母一同住到那个地方去,那已经是很长远的事了,那时树林一直延伸到他的孤独的茅舍边。他的父亲是做一个有钱人的猎地看守人而住到那里去的。可是那有钱人因为穷了,便把一大部分的树林砍伐了变卖。只有那个不值钱的小屋子,却还留在那里。濮佛尔的父母在那小屋中一直住到死,在父母死后,他还一个人住在那儿,因为他已习惯于这一类的生活,他并没有其他欲望,因为他已不复能想象另一种生活了。
他有几只给他生蛋的母鸡,一只他所渐渐饲肥的小猪,一只他用来牵手车的狗,一只给他捕鼠的猫。他也有一只关在小笼中在晨曦之中快乐地唱歌的金丝雀,和一只猫头鹰——这是一位阴郁的怪客人,它整天一动也不动地躲在一个阴暗的巢里,只在黄昏的时候出来,张大了它的又大又圆的猫眼睛,满脸含怒地飞到小玻璃窗边去,等濮佛尔把它的食料放到它的爪间去:田蛙,瓦雀,耗子。
此外,他周围便一个生物也没有了。在他亲自开垦的荒地的一角上,他种了马铃薯,麦子,蔬菜;他到很远的树林中去打柴生火。一大堆由四块粗木板支维着的干草和枯叶,便算是他的床。
他的衣衫是泥土色的。
他的身材不大也不小,微微有点佝偻,手臂异常地长。他的胡须和头发是又硬又黑,他的颧骨凸出的瘦瘦的颊儿,呈着一种鲜明的酡红色,而在他的鲜灰色的眼睛中,有着一种狞猛和不安的表情。
永远没有——或几乎永远没有一个人走到他住所的附近去;如果不意有一个到来的时候,濮佛尔便胆小地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好像怕中了别人的咒语似的。这样,他竟可以说失去了说话的习惯了;他只用几个单字唤他的牲口的名字。他的狗名叫杜克,他的猫头鹰名叫库白,他的猫名叫咪,他的金丝雀名叫芬琪。在他的心灵中,思想是稀少而模糊的,永远限制在他的孤独生活的狭窄的范围中。他想着他的母鸡,他的猪,他的马铃薯,他的麦子,他的工作,他的狗,他的猫,他的猫头鹰。在夏天的平静的晚间,他毫无思想地蹲在他门前的沙土上,眼光漠然不动地望着远处,抽着他的烟斗。在冬天,他只呆看着炉火,陷入一种完全的无思无想的状态中。他有时长久地望着那缩成一团打着鼾的猫,有时在那从小窗中穿进来的苍茫的夕照中坐到那猫头鹰旁边去,看它吞食着田蛙和小鸟儿。
他没有钱,他甚至连钱的颜色也没有看见过,可是每当他的猪肥胖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或是他的鸡太多了的时候(这是每隔四五个月会有一次的事),他便把它们带到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去,去换各种的食物。他很怕这种跋涉,因为他一到的时候,那平时很平静的村子顿时热闹起来了。
顽童们远远地看见他带着那牵着装满了东西的小车的狗到来的时候,便立刻大嚷着:“濮佛尔来了,濮佛尔来了!”于是他们便喧嚷着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面,有的人学着他的犬吠,有的人学着他的猪叫,有的人学着他的鸡鸣。那时濮佛尔又害羞又害怕,红着脸儿,加紧了步子,眼睛斜望着别人;他跑得那么地快,以致他手车的轮子碰到了他的狗的尾巴,而使它哀鸣起来。他尽可能快地穿过了一排追逐着他的顽童,和一排站在门口的嘲笑他的乡民,赶紧跑到猪肉杂货铺去躲避。
在那里,他躲过了残酷的嘲弄。人们称他的猪,人们和他论猪价,接着他便用他的猪价换了各种的货物:第一是一只他可以重新饲养大起来的小猪,其次是猪油和香料,内衣或其他的东西,牛油,面粉,咖啡,烟草,一切他长期的孤独中所需要的东西。
此外,杂货铺的老板和老板娘还请他喝一大杯咖啡,吃白面包饼和干酪,然后送他到门口,祝他平安(话语之间却不免也混着一点冷嘲)。接着,喜剧便又开始了:濮佛尔刚托起了他的手车的扶柄,开口赶他的狗的时候,站在路对面的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们便哄然笑起来了。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车轮下放了一块砖头,因此他怎样拉也不能把车拉动;他愚蠢地微笑着,摇着他的头,好像这每次都是一般无二的恶作剧,还很使他惊讶似的;接着他放下了扶柄,费劲儿搬开了砖石,然后动身上路,不久又像初到时似地跑起来,身后跟着一大群的顽童,一直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才没人跟他。
他这样地在一种完全的孤独中度过了许多年单调的生活,一直到一个奇特而混乱的日子,那一向离他很远的人类生活,似乎亲自走近到他身边去。
有一天早晨,许多人在他的寒伧的茅屋附近显身出来。那是一些很忙的人,在荒地上跑来跑去,手中拿着长铁链和红漆的杆子;他们把那些杆子东也插一根,西也插一根,接着他们又很小心地远远望着那些杆子。
那惊惶失措的濮佛尔躲在他的小玻璃窗后面。他一点不懂得那是怎么一回事,可是他不久看见一个穿着城里衣裳的人,后面跟着一个工人,向他的小屋子走过来。立刻,有人敲他的门。
“有人吗?”别人在外面叫。
濮佛尔先是装做听不见,不愿意去开门。
可是外面打门打得愈急了,他只得走出去。
“朋友,”那位先生很客气地说,“你可以给我们设法找几根细木棒吗?我们现在正在测量那要从这里经过的新铁路。”
“啊,可以,先生。”濮佛尔用那他自己也听不清楚的低低的嗄音回答。他到他的小屋后面去找了几根细木棒来交给那工人。
“谢谢你,”那陌生人微笑着说,“你可要抽一根雪茄烟?”
“你太客气了。”濮佛尔用那同样的嗄声回答。
那陌生人拿了几支雪茄烟给他,接着用一种胜利的声音对濮佛尔说,好像他的话会使濮佛尔很快活似的:
“以后这里不会这样荒凉了,我对你说!”
那眼睛苍白,畏人而充满了不安的濮佛尔没有回答。
“我们在此地筑路。”那陌生人补说着,作为上面一句话的解释,同时向那个奇特的人斜看了一眼。
可是濮佛尔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于是,说了一声“再见,我们晚上把你的木棒拿来还你”,那陌生人便带着他的工人走了。
一条铁路!濮佛尔想着,他害怕起来。这条铁路在尚没有存在以前就深深地使他不安了。
他多么地希望那条铁路不通过来!过着隐遁生活的他,很怕那些老是嘲笑他的人们来临。然而,在他的心中却起了一种好奇的情感,这好奇的情感不久又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热烈的愿望了。
他先逃到树林中,可是他的恐惧渐渐地减小下去,竟至不久去看那些人们工作,甚至和那些实在对他无害的陌生人们说起话来。
“呃,濮佛尔,”他们开着玩笑说,“路一筑成之后,这里可要变成很有味儿的了,可不是吗?那时你便会老看见那些漂亮的火车开过,车里坐着国王们,王子们,公主们。”
“那么附近会有一个车站吗?”濮佛尔问。
“不,这条路只是用来缩短特别快车的路程的。可是,哙,”他们开玩笑说,“只要你用你的手帕打一个号,火车便随时会停下来。”
“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火车。”濮佛尔回答。
于是他便沉思般地回到辽远的树林那边去。
他不久看见火车来到了:那是一些小小的机车,叫起来声音很尖锐,曳着一长列的没顶货车。人们从那里卸下一大堆一大堆的沙土、枕木和钢轨。他并不害怕;只是他一点也不懂,又十分惊佩。最使他惊异的是那些沉重的车子那么听话地沿着那两条铁轨走,而永远不翻倒。
“怎样会有这样的事!”濮佛尔想。于是他常常去看,心想那车子随时会闹出一件意外事来。
没有意外事闹出来。成着直线,穿过了荒地和树林,那条路线不久便从这一端地平线通到那一端地平线,最后竟可以通行华丽的大火车了。
行落成典礼的时候,濮佛尔也在场。
他是在铁路的路堤下面,和几个筑铁路的工人在一起。在那铁路迤逦而去的天涯,有一件像是一头喘息着的黑色小牲口似的东西在动着,又似乎异常匆忙地赶来;接着,它好像被怒气所胀大了似地一点点地大了起来,飞快地跑上前来,它不久变成了一个怪物,把火吐在地上,把烟喷到空中,像一个骚响的大水柱似的经过,带着一片蒸气和铁的震耳欲聋的声音,简直像是一个大炸弹。
濮佛尔喊了一声,腿也软下去了;他张开了他的臂膊,好像受了致命伤似的,晕倒在地上。
那些做着手势,向那经过的火车高声欢呼着的铁路工人们,嘲笑着那不幸的濮佛尔。
“什么都没有碰碎吗?你还活着吗?”
那害羞的濮佛尔一声也不响地站了起来,蹒跚地向他的小屋子走过去。
那些几个月以来在那个地方工作和生活的人们,现在都已经走了。濮佛尔又恢复了他的完全的孤独,只有每天四次,早晨两次和下午两次,受着那从两面开来的国际大列车骚扰。而那不久已克制住自己的最初的恐惧的濮佛尔,常常去看它们有规则地经过。在那大怪物要出现的时候,他既不能留在荒地中,又不能留在他的茅屋中。他走到路堤上去,望着天涯,俯卧在地上,耳朵贴着铁轨。于是他便听到铁轨歌唱着,它们为他而唱着神奇的歌。它们唱着一个濮佛尔所没有到过,也永远不会插足的荒诞的世界,一个广大无穷的世界。它们永远一动也不动地躺着,唱着它们的温柔而哀怨的歌;可是当火车走近来的时候,它们的歌便变成生硬而格外有力了,好像它们突然被从它们永恒的梦的温柔中赶了出来一样。它们不久便战栗起来,发出了苦痛,暴怒和复仇的尖锐的呼声。火车已在那边了。黑斑点也在天涯现出来了。那是永远像第一次一样的:一头喘息着的小小的黑色的牲口,像被自己的怒气所鼓胀起似的,动着而渐渐地大起来,大到像一个巨大的怪物,像雷霆一样地滚着,用它的尖锐的声音撕裂了空间,接着便隐没在一种铁器和蒸气的地狱一般的声响中。
濮佛尔退了十几步,呆望着那种光景。好像在一片闪电中似的,他瞥见了一点火车的生活:人们填进煤去的那怪物的大嘴,张望着天涯的机车手,和在那长长的华丽的列车中的,人类的侧影的手势和姿态:抽着烟的先生们,横在红色的坐垫上的身体,坐在玻璃窗前的先生们和太太们,在吃饭的夫妇们,男的是又红又胖,女的是又纤细又窈窕,穿着鲜艳的衫子,戴着深色的帽子,弯着身体,微笑着。
那些铁轨所歌唱的伟大的生活,他所完全不知道的神奇的生活,便是在那里;他只瞥见了这生活的一闪转瞬即逝的侧影,他永远不能近看它们。哦,他是多么愿望仔细看它们!他是多么愿望这华丽的火车停下来(就只是一次也好),去见识见识那神奇而陌生的生活中的一点儿东西!这个任何世界的秘密也不知道的人,这个一生在孤独中过去的人,这个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美丽的妇人的人,这个永远没有见过一个大城市的人,这个永远没有尝过佳肴名菜的人,他是多么地愿望这些啊!……他因而感到了一种怀乡病之类的心情,一种缠人的病态欲望。他每天早晨,每天下午都在那儿,眼睛里充满了羡望,像是一个乞丐。火车中的办事人员不久认识了他,看见他老是站在同一个地方,在茅屋的附近,便真的把他当作一个乞丐了;有时人们竟从餐车里丢出一点东西来给他,一块面包,一瓶啤酒,或是一些残肴。他老是站在那里,在白昼或黑夜,带着他的什么人也不知道的那么奇异的愿望,他的对于那些华丽的列车,对于那第一次向他显露出来的陌生的伟大的生活的旷野的急流的,怀乡病一般的愿望。
十一月的一个下午,他照常在路堤上等待着,脸儿向着那光线的辽远的闪烁,向着那火车要从而开过来的南方。夜是凉爽而清朗,满天都是星辰。在天涯边,一弯细细的新月把它的微微有点幻梦似的光倾泻在树林的暗黑的梢头。一种平静的和谐的氛围气摇荡着夜。朦胧的天空和树林的幽暗的线条混在一起,不能互相分辨出来,在远处,铁路的闪光和星光交辉着。
濮佛尔蹲在地上,把他的耳朵贴着铁轨。它们正歌唱着它们的微微有点忧郁的歌。他好像觉得这平静的和谐,是不复会被打破,而那无疑已误点了的火车,是不复会再来了。
而那在平时没有时间的观念的濮佛尔,心里想着:今天它那么迟还没有来!于是他感到了一种悲哀和一种苦恼,好像预感到一件灾祸一样。可是在天涯的尽头似乎有一个光在眨动,而那突然唱得更尖锐的铁轨,又似乎在他的耳边呼着:“是的,是的,我到了,我到了……”
那便是火车。在黑暗中,濮佛尔辨不清楚那个喘息着的黑色的小牲口,可是,看见了那突然扩大起来的,好像受了一片飓风的吹打而摇荡着的光,他似乎觉得那火车跑得异乎寻常地快。在车轮的噪音之下,铁轨吼着,土地震动着;那光线变成了一个炯明的火炬,一片猛烈的炭火,四面喷射着火焰和蒸气的舌头;接着,突然发生了一种在地震中的噩梦的幻象:一大堆红色和黑色的东西带着一种骇人的霹雳声倒了下来,一片钢和铁。打碎的声音,木头飞裂的声音,玻璃碎成片片的声音,而在这巨大的声音之间,还夹着人类的声音的绝望的呼声……像一个梦行人一般地,濮佛尔大喊着逃到荒地那面去;接着他又像一个梦行人一般地走回来,把拳头放在鬓边,眼睛凸出着,在那机关车的震耳欲聋的汽笛声中呼喊着,啼哭着,呜咽着;那机关车躺在那里,陷在泥土中,上面压着破碎的列车,像一头快死的大牲口似地喘着气,吼着。他倒了下去;他站起来,可是接着又跌倒了,浴身在一种温暖而发黏的流质中,被尖锐的破片所刺伤,在烟和火焰中窒息着,在奔逃的人们的呼声中呼喊着,在受伤的人们和垂死的人们的残喘中呼喊着,在机车的继续不断的怕人的汽笛声中呼喊着。
于是他飞也似地奔跑着逃到他的茅屋那里去。
“现在我看见过了,我看见过了!”他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