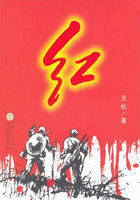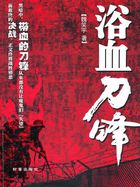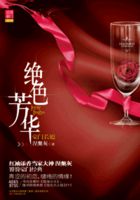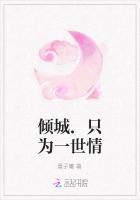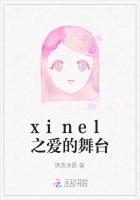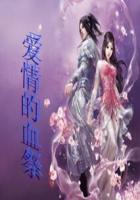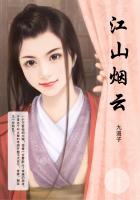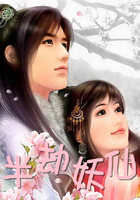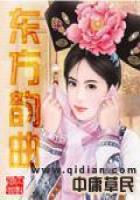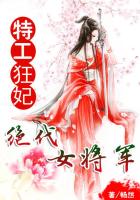时间回溯到1958年2月,毛泽东主席刚刚钦点了极富传奇色彩的独臂将军余秋里,命其主政石油工业部;几天后的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听取石油工业部的汇报后冲余秋里说道:“在着重建设好西部(玉门)石油基地的同时,要对松辽(大庆)、华北(含大港)好好花一些精力,华北、松辽都一样,主要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来。”
余秋里当即表态:“立足于西部,与开发东部并举。”
军中无戏言,石油部立即调整部署,实施了勘探战略的重点东移,并与地质科研部门密切合作,展开了大规模的勘探勘察。于是,地质工作者与石油物探队伍,作为大规模勘探开发华北平原的先行者,开始叩问了这块神奇的土地。
连续的勘探勘察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截止到1966年初,地处首都南大门的凤河营地区的河1井,喜获工业油气流;同年9月,又在河西务的京一井,获工业油气流;于是,指挥部决定再上冀中,并重点选择了河北省的霸州至任丘一线,结果普遍见油,但产量较低,难于投入大规模的开发。
再后来,由于辽宁东部的葫芦岛地区发现储油构造,燃料化学工业部不得已而被迫终止了这里的勘探工作,集中力量去开发建设辽河油田,但这里的地震普查工作并未间断。
正当大庆、辽河石油会战如火如荼之际,燃化部在山东的胜利油田,召开了全国石油勘探开发技术座谈会。会上确定了华北地区以“大战凸起,猛攻灰岩。”的战略方针,并对包括胜利、大港油田在内的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进行了改组,成立了以大港、冀中为主战场的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并把首批重点勘探地域,确定在了河北省保定至沧州至石家庄一线的高家堡、任丘、高阳、留路地区。
所属第二钻井指挥部的一支钻井队,不负重望,首先在高家堡的家1井,获得了日产50吨的高产油井。这个钻井队正是魏大力带领的3269钻井队。
这之后,魏大力又带队转战石门桥,抢上任4井;而与此同时,河北地质局3505钻井队,在任丘的冀门1井喜获良好油气显示;
根据上述捷报,1975年4月,主政石化部的康世恩,提出了重点勘探任丘、霸县、河西务的实施方案,这才有了张文斌临危受命,一场大战的序幕徐徐的拉开了。
就在几个月之前的1975年6月,任4井完钻,并打入了古潜山,7月份经过试油和酸化,获日产原油竟达1014吨。
惊雷炸响,捷报频传。
这可是石油人梦寐以求的“大金娃娃!”
“太好了,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正在大港油田招待所休息的张文彬,得到消息后,欣然披衣而起,他连夜调兵遣将,直到天明也没有了睡意。
这才有了前文,张文彬来到海边,目睹一浪接一浪的大海,以及海平面冉冉升起的一轮红日,满怀踌躇,激情勃发……
与张文斌同期到达任丘总部会议棚的,还有大港油田研究院工程师杨培山等四名科技专家,他们担当了战役的先行官,确立了油田开发的重点和总体设想。
张文彬与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举行了一个短暂的碰头会,交换了一下意见之后,立即带领杨培山等人,驱车赶往3269钻井队。
此时的3269钻井队,自任4井出油后,已转战至任6井。全队干部职工,正在队长魏大力的带领下,披星戴月的紧赶进度。
几十公斤重的大钳,在魏大力手上旋转如飞,夕阳的余晖映射着他淌满汗水的脸,此时的他已经46岁了。
这时,二层平台上扶钻杆的一名工人朝他喊:“队长快看,来了辆小车!”
魏大力听见喊声,用衣袖抹了把脸上淌满的汗水,抬头见井场外面的泥土路上,一辆伏尔加轿车正风驰电掣般的驶来,他知道是来大人物了。
车子驶进井场,刚一停稳,一位身材矮胖,头发花白,披一件早褪了颜色的旧棉工作服的中年人,走下车来。
魏大力一见,“哎呀!”一声,把大钳递给身旁的一名工人,自己三步两步就跑下了钻台,来到张文彬跟前,两腿一并,“啪地”一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