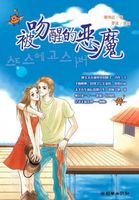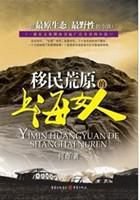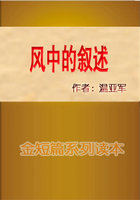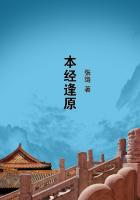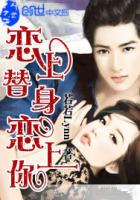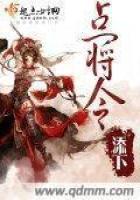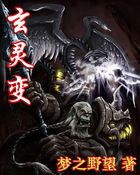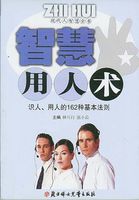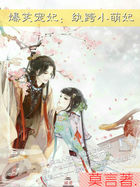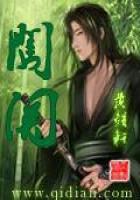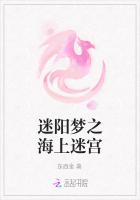誓师大会之后,华北平原捷报频传,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就如同一浪高过一浪的海浪一般。自任4井,任6井出油后,任7井、任8、任9……任11井、先后出油。其中任11井,采用高浓度、大酸量、快排酸的措施,酸化压裂成功,日产竟达4021吨。
紧接着任9井,酸化、试油完成,获日产原油5400吨以上,成为任丘地区,乃至全国各油田单井产量最高的一口井。
然而在年初,尤其是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作为石化部副部长,兼冀中勘探开发党组核心人物的张文彬,尽管一个接一个的喜讯,如同雪片一般的飞来,可他却始终双眉紧锁,脸上没有用一丝笑意,他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虽然任4井、任6井、任9井、任11井等等都实现了开门红,抱了大金娃娃,然而接下来要办的事情更多、更复杂、更棘手。
此时此刻,正当他在地图前凝神思索着油田的面积和油层的厚度究竟有多大的时候,石化部突然下达了新的任务:第一,设想从现在起用三个季度或半年的时间,再抱20个左右的金娃娃;用一年的时间,力争建成年产100万吨的大油田;第二,战斗在南马庄构造带、留路构造带的各个钻井队,要加快速度,尽快拿出勘探成果;第三,打高家堡家3井的4064钻井队,要下决心打成4500的深井,从而摸清地质构造。此外,我们拟定向全国各油田抽调队伍,重点放在石家庄以北的深泽,保定以东的高阳,力争发现新储量;同时,你们要在北京附近廊坊一线的旧州、固安、河西务一带展开勘探,如能在首都的南大门打出高产油井,其意义更为重大……
历史有时候往往会给当事人,开一些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的小玩笑。就上述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三大任务”而言:尽管在早已完成和实现、并成为了历史今天,回想当初仍感震惊和悍然,因为当时,作为开发新区主帅的张文彬,三大任务具体出台的原因和细节,并不是十分清楚。
这就奇怪了,按照常理,一个新油田的开发建设,首先要取得一定的数据,最起码也要了解油层厚度、面积、储量、然后再制定合理的实施方案,正规开发。
但是,那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年代不能过分强调规律,规律还要向政治让路,还要批“唯生产力论”。
事实上,石化部早在1975年以前,按照所制定的年产8700万吨的原油生产计划,一直就欠产。这样一来,任丘油田如果不尽快上马,势必依然完不成任务。
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说当年的石油部在国家“一五”期间完不成任务,那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那么1976年要再完不成任务,是必要被归咎为政治因素。
早在6月份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张春桥得知石化部欠产,当场就大发雷霆,指着主管生产的副部长孙敬文质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要好好总结思想。”
时过境迁,也许正是当年石化部强下的这个三大任务指标,促使一个大油田快速矗立在距首都北京正南100多公里的大平原上。
然而当初,这无疑给主政华北的张文彬,面对人员、物资、后勤保障均不到位的情况下,展开这么大规模的石油会战,这不亚于千钧重担。然而,重担归重担,再大的困难也决不后退,没有困难就干不成大事;没有压力就达不成目的。这是他张文彬的性格,也是新区领导班子的性格,更是几万几十万石油大军的性格。
“要开个会,一定要开个会。”张文彬想,他首先与党组成员任成玉同志交换了意见,又与其他班子成员:马永林、毛华鹤、孙德福、李全亨、唐克伦等进行了沟通。
于是,1975年12月27日,在大港油田3号院,召开了旨在全面贯彻落实“三大任务”的“夺取明年首季开门红誓师动员大会”,并要求全体参战的干部职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认清形势、紧急动员起来、横下一条心,上下齐努力,坚决完成“三大任务”这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也为大上华北雷响了战鼓。
时间悄然进入了公元1976年。
这一年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讲,可谓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离世。巨星陨落;唐山大地震,又使数十万生灵,化为乌有。神州大地泪飞如雨,江河日月为之呜咽。
然而这一年,又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的一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国民经济逐步走向正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无处不飞歌,无处不欢笑。
诚然,人们只记住了这些大事记,可有谁能知道?有谁能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有这样一大群人,他们脚蹬大皮鞋,身穿道道服,头戴狗皮帽子,共同拥有一个名字——石油人,满怀一腔热血,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为了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崛起,他们搭帐篷、钻管沟,头顶青天,脚踏荒原,要在这“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地的平原大地上,上演一出新世纪撼天动地的慷慨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