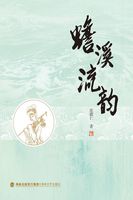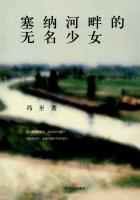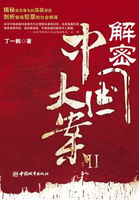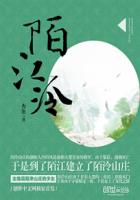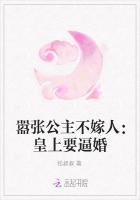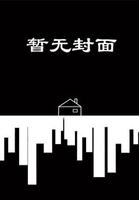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夫圣人之为经,惟其《礼》与《春秋》合,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春秋》之严矣。而况《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无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
今之《诗传》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藟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已劳矣。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时,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雷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比、兴。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当时之事。则夫《诗》之意,庶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礼论
昔者商、周之际,何其为礼之易也。其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荐,交于堂上,而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让,献酬百拜,乐作于下,礼行于上,雍容和穆,终日而不乱。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间,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于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乐之意,故其廉耻退让之节,睟然见于面而盎然发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观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气。
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详其节目,而习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习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
昔者上古之世,盖尝有巢居穴处,污樽抔饮,燔黍捭豚,蒉桴土鼓,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及其后世,圣人以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宫室,新之以笾豆鼎俎之器,以济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荐其血毛,豚解而腥之,体解而爓之,以为是不忘本,而非以为后世之礼不足用也。是以退而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簠簋笾豆铏羹,以极今世之美,未闻其牵于上古之说,选愞而不决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为,而天下之人亦且见而笑之,是何所复望于其有以感发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庙之祭,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灵,庶几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饮食之际,而设其器用,荐其酒食,皆从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而后世宗庙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则是先祖终莫得而安也。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虽正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为便安。
故夫三代之视上古,犹今之视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复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仿以为法也。宗庙之祭,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有以存古之遗风矣。而其馀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从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释奠释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则皆从其器,盖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吹苇籥,击土鼓。此亦各从其所安耳。
嗟夫,天下之礼宏阔而难言,自非圣人而何以处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讲之而不详,则愚实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几天下之安而从之,是则有取焉耳。
春秋论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覆,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
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
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馀年矣。愚尝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其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
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求其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怨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泄。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
至于《公羊》、《榖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吴仲孙”,甚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
中庸论三首
上
甚矣,道之难明也。论其著者,鄙滞而不通;论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于昔之儒者,求为圣人之道而无所得,于是务为不可知之文,庶几乎后世之以我为深知之也。后之儒者,见其难知,而不知其空虚无有,以为将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则从而和之曰然。相欺以为高,相习以为深,而圣人之道,日以远矣。
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为性命之说。嗟夫,子思者,岂亦斯人之徒欤?盖尝试论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从以为圣人,而其虚词蔓延,是儒者之所以为文也。是故去其虚词,而取其三。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盖以为圣人之道,略见于此矣。
《记》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夫诚者,何也?乐之之谓也。乐之则自信,故曰诚。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谓也。知之则达,故曰明。夫惟圣人,知之者未至,而乐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乐之者为主也。若夫贤人,乐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为主,而待其馀,则是知之者为主也。乐之者为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行。知之者为主,是故虽无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者与乐之者,是贤人、圣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贤人之所由以求诚者也。君子之为学,慎乎其始。何则?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乐焉,则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恶,莫如好色而恶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恶恶如恶臭,是圣人之诚也。故曰“自诚明谓之性”。
孔子盖长而好学,适周观礼,问于老聃、师襄之徒,而后明于礼乐。五十而后读《易》。盖亦有晚而后知者。然其所先得于圣人者,是乐之而已。孔子厄于陈、蔡之间,问于子路、子贡,二子不悦,而子贡又欲少贬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乐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于卫,而不能不愠于陈、蔡,是岂其知之罪耶?故夫弟子之所为从孔子游者,非专以求闻其所未闻,盖将以求乐其所有也。明而不诚,虽挟其所有,伥伥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则是可与居安,而未可与居忧患也。夫惟忧患之至,而后诚明之辨,乃可以见。由此观之,君子安可以不诚哉!
中
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故曰“莫若以明”。
使吾心晓然,知其当然,而求其乐。
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用器之为便,而祭器之为贵;亵衣之为便,而衮冕之为贵;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乐欲其不已,而不得终日:此礼之所以为强人而观之于其末者之过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将惟安之求,则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则将裸袒而不顾,苟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苟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夫岂惟磬折百拜,将天子之所谓强人者,其皆必有所从生也。辨其所从生,而推之至于其所终极,是之谓明。
故《记》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从生而言之,则其言约,约则明。推其逆而观之,故其言费,费则隐。君子欲其不隐,是故起于夫妇之有馀,而推之至于圣人之所不及,举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难,使天下之安其至难者,与其至易,无以异也。
孟子曰:“箪食豆羹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朋友妻妾之奉而为之,此之谓失其本心。且万钟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难,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较其轻重,是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之所能行,通而至于圣人之所不及?故凡为此说者,皆以求安其至难,而务欲诚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诚,而不得其说,故凡此者,诚之说也。
下
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记》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终日安行乎通途,夫虽欲不废,其可得耶?《记》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以为过者之难欤,复之中者之难欤?宜若过者之难也。然天下有能过而未有能中,则是复之中者之难也。
《记》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执中为近。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书》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又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记》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皇极者,有所不极,而会于极;时中者,有所不中,而归于中。吾见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归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为时中,而小人之所以为无忌惮。《记》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嗟夫,道之难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窃其名,圣人忧思恐惧,是故反复而言之不厌。何则?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窃以自便者也。君子见危则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于中庸。见利则能辞,勉而不辞,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原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为足以已矣,则是不亦近似于中庸耶?故曰:“恶紫,恐其乱朱也,恶莠,恐其乱苗也。”何则?恶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难言也。君子之欲从事乎此,无循其迹而求其味,则几矣。《记》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