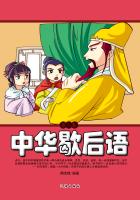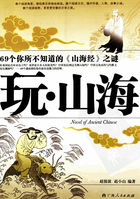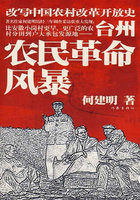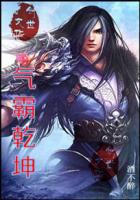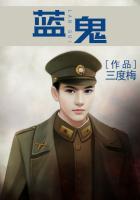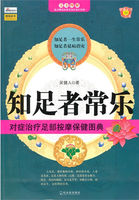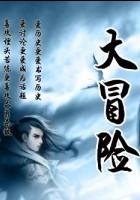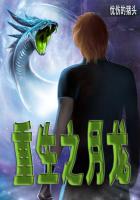所谓“风俗”,《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连对这层意思的表达也都略有差别,在我们湖北老家的说法就是“路隔五里,乡俗不同”。
惠州是我国客家人比较集中的城市之一,而客家人保留的传统风俗,大多是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移民带来的。我们这些外来者,在慢慢融入这些风俗时,就有了故事和记忆。
几年前,我带着昔日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千里奔来惠州。凌晨,我们从惠州火车北站进入这座城市,点点灯火下,这片将要接纳我的土地,香香地熟睡着。
刚到惠州时,我们与单位的一帮同事住在一起。房子是老板租来的,还请了个阿姨做午饭和晚饭。刚开始吃惠州口味,觉得清淡不已,什么菜都看不到辣椒。再就是每餐饭阿姨都要煮一大锅汤,汤料让初来乍到的我们尤觉惊奇。有时候是苦瓜和排骨一起,里面点缀几颗黄豆;有时候又是枸杞叶,里面搭配几片猪肝;最奇怪的是一种像草根一样的东西,居然也可以用来煮汤,后来知道那叫鸡骨草。而煮汤也不能说是“煮”,应该叫做“煲”。
吃的方面,没用多久,我们就慢慢适应了。开始还去超市买点辣椒酱,在吃饭时调节一下口味,后来这笔钱也省了下来。吃饭前,我也习惯喝点汤,遇到好汤,喝一碗还不尽兴,眼巴巴望着硕大的汤罐或汤碗,希望能再分一杯羹。
语言交流方面,倒没觉得怎样生分,感觉惠州的包容性很强。在最初的单位,有些人讲广州话,本地人讲客家话,也有人讲潮汕话,但工作与交流时,大家就都用普通话了。土生土长的街坊邻里,普通话也讲得不错。有一次,我们去市场买菜,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守着几网兜从东江摸起来的花甲、坑螺等河鲜,招呼我们时叽里咕噜听不懂。我们开口问价,她听我们讲普通话,就马上换成了普通话。
吃喝习惯、交流方式是风俗,但根深蒂固的风俗,还是凝结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些凡人俗事中。后来,我进入到现在的单位,并顺利留在了还算喜欢的惠州。几年过去,买房、结婚、生小孩,惠州的风俗正一点一滴的融入我的生活。前不久,给女儿摆满月酒,都基本按照惠州本地风俗,就是宝宝的禁忌,妈妈要喝鸡酒、吃猪脚醋等,都是纯正的惠州风俗了。
一老友在博客上写了篇“在外面想家在家想外面,草根白领陷入‘思乡围城’”的文章,说是如今有越来越多为了追求梦想、“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年轻人,一边感叹难以融入异乡,另一方面却又开始不习惯家乡,最终陷入“思乡围城”的尴尬。
的确,思乡是一道难解的题。故土难离,思乡情怯,其实根源在于未能融入当地风俗。我想,既然已经陷入“围城”了,不如主动去适应它,入乡随俗,向所在之地的风俗靠拢,接近它、吸收它直至让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也许依然剔除不尽血液里的故乡情结,但它应该会造出新的血液来,最少能让生活不至于总在尴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