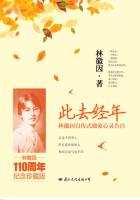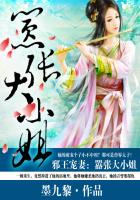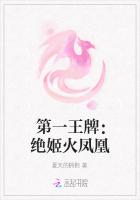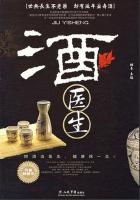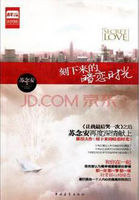在世界文化史上,被本民族引以为文化巨人的并不多见,至于像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康德、黑格尔、托尔斯泰等被视为世界文化巨人的更为罕见。一般来说,文化巨人是吸收了本民族优秀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乳汁,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里成长起来的,文化巨人一旦产生,便常常代表着本民族文化的方向,成为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在中华民族这块古老的文化土壤里曾经孕育了孔子、鲁迅那样的文化伟人,被世界所注目和津津乐道,虽然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对立的文化巨人:一个是传统文化的代表,一个是新文化的代表,但他们都曾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方向、核心和灵魂。因此,对他们的研究便成为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试图对两者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以区别巨人文化和圣人文化,这对加深认识孔子和鲁迅各自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或许有所裨益。
(一)
虽然至今我们还未能找到一种为大家所满意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文化的研究和讨论的兴趣。当我们从理论上将“文化”列入哲学范畴系统时,我们便将它全部的丰富性和完整性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和人类活动现象的文化的内容,而依据创造文化的主体的不同规模来划分文化的类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文化从日常生活和科学的涵义上分为:(1)人类文化;(2)一定社会类型的文化(如古希腊文化、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美国文化等,往往局限于某种空间和时间);(3)集团文化(包括民族文化、阶级文化、民间文化、种姓文化、家庭文化等);(4)个体文化,个人的文化。
无疑,个体文化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没有个体文化,一切文化都是仙山琼阁。个体文化依据自身的力度或大或小地与集团文化、一定社会类型的文化、人类文化发生相互影响,因而它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个体文化能够演变为民族文化的却甚为罕见,这种奇迹仅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出现过两次,这就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和鲁迅建立的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两种根本对立的个体文化——圣人文化和巨人文化,竟神奇般地同为人们所敬仰,应该说,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如果我们不苛求古人,那么可以说,孔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个文化巨人,他的一些思想至今还为人们所赞赏,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孔子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出色的私塾教师,一个教育家,一个想为统治阶级效劳而终生不得志(尽管也做过几天官)的穷困潦倒的思想家。他活着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作为,死后却吉星高照。他创立的儒家学说竟居于众家学说之首,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他本人甚至被尊奉为圣人,他的学说也被蒙上了一层圣光,成为圣人文化而经久不衰,被看成是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化,看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文化信息源。
其实孔子的学说并不神秘:他没有什么系统的著述,他的思想也完全称不上有什么严密的体系,但它始终是以仁、礼、中庸为核心,围绕道德观念展开的,属于伦理型的个体文化。
主张忠于君王。孔子说:“事君尽礼”,“臣事君以忠”。这种忠君思想适应了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以至于后世儒家的忠君思想越来越严格,甚至提出“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观念,这种愚忠观念断送了封建社会中不知多少廉洁正直而又顺从君王的士大夫。
主张孝敬父母。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这种孝敬父母的思想随着宗法制的发展,达到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愚孝程度。
主张对他人施行仁爱。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仁”的最高标准是“博施济众”。这种仁爱思想曾被历代一些开明的统治者和改革家重视,促使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关心人民疾苦,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力的发展。
主张重义轻利。孔子说:“见利思义”、“义德后取”。这就是说一利在前,符合正义的才能取,不可见利忘义。这种重义轻利的思想在后期儒家发展到了禁欲主义的程度,理学家甚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
孔子对伦理道德的重视,还表现在他对礼的推崇上。他认为人们的思想感情、言论行动决不能越过“礼”的界限,应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主张人必须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任何时候都应该“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即使对恶人也只采取从容中道的态度。
孔子的这种伦理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子学、经学、理学等各具特点的理论形式奠定了带有浓厚伦理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当然不能无视它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里曾经起过的重要作用。儒家文化,或者说圣人文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产生的,或者说它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狭小的农民经济,它在内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巨大的保持自身固有平衡的能力,而不易在外部联系中破坏自身的发展和运动。中华民族对自身的整个平衡的要求(如在封建专制政治基础上的平衡,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平衡等),也体现在这种主要经济形态基础上的平衡。这种平衡含有较多的理性成分,笼罩着中庸之道的灵光,儒家文化恰恰与这种平衡的和谐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因此,它在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大一统,为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民族追求内部平衡而自立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成为一个稳定的文化系统,这不能不是孔子伦理文化的功劳,它显示了孔子的个体文化演变为民族文化的奇迹。
使人感到有趣的是现代文化巨人鲁迅对相距遥远的孔圣人却大不恭敬,在他的著作中常常以一种嘲讽的笔调毫不留情地将孔子赶到不光彩的一类历史人物中去,他以现代人应有的眼光和他异常清醒的文化意识居高临下地鸟瞰着中华民族全部的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和他的后人。他以超人的勇气,在与黑暗势力的决战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彻底的决绝的否定,从而形成了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产生了一代新的巨人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让人深思的是鲁迅进行批判和否定的传统文化恰恰正是孔子创立、后人发展起来的伦理文化,鲁迅抓住其核心——仁义道德,全力以击之,可谓击中了要害。鲁迅的每一部著作都可以看成是埋葬旧文化的战斗檄文和无情的判决书,他对中华民族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是他人难以企及的,难怪才华超人的郁达夫也感叹道:要了解中国,除了读鲁迅的书,别无他路。
鲁迅虽然生在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受着严格的传统教育,但他有幸接触了《山海经》、野史之类的民间文化,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叛逆的种子,因此一有机会,就要摆脱传统教育。他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倒是使他“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而这恰恰是儒家文化所缺少的。
鲁迅成年后,更自觉地向“今世之学”进军,特别在五四中西文化相互撞击和交汇的漩涡中,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缺少的反传统精神,为建立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打下了坚定的思想基础。鲁迅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之心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充满了深沉的热爱和真挚的感情,追求民族自立自强的强烈责任感使他对那些狭隘的爱国主义、夜郎自大的民族虚荣心进行了尖锐的嘲讽,为民族落后的原因和难以克服的弱点而痛心疾首,对那种置民族命运和前途于不顾而攫取爱国主义美名的丑恶现象给予致命的抨击,以博大的胸怀热情宣传学习他民族的优长,为中华民族在东方重新崛起竭尽全力地呐喊和战斗。因为鲁迅有着这样彻底的反传统精神和深厚的爱国主义,他才没有成为一个学究,而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士。他没有试图建立系统的哲学体系,但他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却深深地在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中扎下了根。
五四时期,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包括对孔子的批评,感情上的因素往往超过理智上、学术上的因素,有一种文化上的历史道德化倾向(这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在一种强大的近乎火山喷发式的批判的群体意识的影响下,鲁迅却依然保持着他异常清醒的头脑,没有在文化意识陷入历史道德化的激情中去,尽管他也站在火山喷发口的前列。他意识到儒家文化与儒教中国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历史现象、两个不同的价值体系,但在传统文化范畴内,它们都带有浓厚的鲜明的伦理特征,都充满非人道的因素。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教中国是儒家传统得以繁衍的母体,而儒家传统又是这个母体中循环往复的血液,维系着这个母体的生存。因此,批判旧的文化传统决不能满足从道德上寻找根源(尽管这也是需要的),而必须彻底在文化土壤的深层处摘除毒瘤和病根,在文化土壤的层面上清除垃圾和芜秽。所以,鲁迅虽然对传统文化有过一些肯定,挖掘过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却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从整体上对旧的文化传统的彻底的决绝的批判和否定。
鲁迅从历史思索的积淀中,不仅将传统文化看做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制造吃人悲剧的文化,而且看成是制造奇妙逃路,进行“瞒”和“骗”的文化体系,是一个单元的封闭的僵硬的文化系统。他还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传统文化是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低级阶段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在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已成为落后的甚至可能导致民族灭亡的危险的东西。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主要集中在他对文化核心层的剖析,即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剖析。鲁迅对“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常常给予痛诋,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人的灵魂(包括改造他自己)、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伟大工程。鲁迅以他巨人的强大透视力由内而外地,即由文化的核心层向文化的外层辐射,又由外而内地,即由文化的外层向文化的核心层观照,透彻剖析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风俗习惯等,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对民族文化的集体心理严肃地加以剖析,在剖析中认识了自己;另一方面,他在毫不留情地对自己的个人文化心理进行解剖的过程中,加深认识了民族。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鞭辟入里的剖析以及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迫切愿望是他人无法相比的,因为这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巨人高瞻远瞩的胸襟和坚韧不拔的信念。鲁迅曾郑重地指出:“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鲁迅正是这种心中充满理想光辉的伟大的文化革新者。
可见,鲁迅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绝不是文化上的历史道德化,更不是文化的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尽管鲁迅曾经十分悲观,特别在《彷徨》、《野草》中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和偏激的声音,但那是他内心对文化传统的巨大压力的强烈反映。他曾叹道:“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因此鲁迅的悲观是对文化传统之强大和顽固以至难以冲破的悲观,而不是文化上的悲观主义。由于鲁迅对反传统的艰难的深刻体验,所以他主张“深沉的韧性的战斗”。他意识到从长远观点看,传统是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障碍,必然要被冲破,但事实上人在现实生活中又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冲破传统的束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必须坚持不懈地反传统。这正是鲁迅超人的地方,也是他被视为文化巨人的主要原因。所以,当我们的民族在寻求自身发展的道路,对传统文化的束缚感到困惑时,鲁迅以文化伟人的姿态崛起于中国历史舞台上而建立的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发挥了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从而代表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巨人文化的又一个奇迹。
(二)
如果凭一部《论语》,便将孔子说成是文化巨人,或许使人感到有些勉强,因为孔子仅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多思想家中的一个,儒家也仅是诸子百家中之一家,其影响在当时并不显赫,况且孔子也没有写下什么鸿篇巨制,留给后人的仅仅是散见的只言片语,且是他的弟子所记,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们评价文化巨人的重要标志,关键并不在于量(虽然量也是一个重要的尺度),而在于质,在于其价值体系。孔子创立发展起来的儒家的知识精华对中华民族素质与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其影响之大,无疑远在百家之上,这是孔子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正因为如此,在不苛求古人的基础上,我们才将孔子看成是古代的文化巨人。
但可悲的是孔子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历史误会,以至于人们已无法搞清楚孔子的真面目。鲁迅早在62年前就指出:“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精辟地论述了孔子被人们所误会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原因,对孔子的被圣化作了深刻的剖析。鲁迅引用了孟子批评孔子的话,把孔子称为“摩登圣人”,认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鲁迅尖锐地抨击道:那些将孔子当做砖头用而遭到失败的人物,“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因而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的精义几乎被“捧”、“抬”的历史浪潮所淹没,孔子的形象也因为“敲门砖”的名声而完全模糊,孔子的个体文化终于成为统治者愚弄老百姓的圣人文化,成为腐败的儒教中国的思想核心,对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一蹶不振,不能不负有责任,尽管它对中华民族的素质和性格的形成、发展有过良好的影响。但即使如此,“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鲁迅断言:“能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
所以,孔子的被误会,孔子的个体文化从巨人文化演变为圣人文化,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在中国文化史上,既是一个奇迹,又是一个悲剧;既是孔子个人的奇迹和悲剧,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奇迹和悲剧。
无独有偶,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被圣化,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鲁迅竟然也曾被神化,让人感到困惑和无法理解。
鲁迅当年曾不无感慨地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悉,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在他死后,终于在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建立了新社会的中华大地上,旧文化传统的恶习竟有机会像瘟疫一样传染和膨胀起来,他也像孔夫子一样被当着了“敲门砖”的差使,他的形象被践踏,成了一个无所不斗而又斗无不胜的凶神,他的思想被歪曲,他的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仅仅成为斗争的哲学,一本充满火药味儿的“鲁迅语录”跟一本“红宝书”一样具有魅力,他的被“捧”被“抬”也终于到了跟孔子一样的地步。于是,鲁迅被人们误会了,虽然先前人们对他也有过种种误会,但从来没有像这样被误会,成了社会的一个畸形巨人,这不能不是中华民族的又一个悲剧,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黑暗的一页。值得庆幸的是这黑暗的一页很快就翻过去了,鲁迅又得以复归返真。但是,鲁迅的真面目却还没有真正完全被人们所认识,人们对他的误会还没有完全被消除,他的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对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引导和表率作用,还没有完全被人们重视,一句话,也就是巨人文化的价值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挖掘。
(三)
现代社会越发展,越需要产生文化巨人,而又越难产生文化巨人。产生文化巨人,是一个民族的骄傲,但是产生文化巨人,则又可能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能是单元的,必须是多元的,只有多元,这个民族的文化才可能是充满活力和蓬勃生机的,如果让巨人文化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方向和灵魂,就有可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成为单一的封闭的僵化的文化。因此,我们需要文化巨人,重视巨人文化,但不希望巨人文化演变为民族文化的代名词和同义语。
今天,当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向孔子和鲁迅这两个根本对立的文化伟人时,我们不能不对这两个不同的历史现象和价值体系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作一番审慎的探讨。
推崇孔子的人们,尤其在海外,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伦理上的、学术上的,掀起了一股振兴儒学热,大有儒家席卷天下之势,以为儒家传统可以解决现代社会遇到的种种矛盾,这无疑过分抬高了儒家学说,倘若孔子在,也会瞠目结舌的。儒家文化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人类社会,如果真的能解决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旧中国还会沦为腐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吗?
孔子的时代毕竟早已成为历史,我们用不着再用种种白粉去涂抹孔子了,应当还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家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分析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在学术上和文化史上给它以一定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回头看历史,不能将目光停留在历史上,而应当投向现在,投向未来。我们的主要精力应花在现代科学上,而不能消耗在传统上。
同样,鲁迅——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先驱者,20世纪初中国的但丁,也已成为历史,他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作为反对封建思想和专制制度的产物,有着鲜明的过渡特征,因此,要解决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遇到的种种困惑,也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不可避免地带着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种种痕迹,因此鲁迅的带着强烈反封建色彩的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仍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然而,这并不是一件令人乐意的事,早在1926年,鲁迅就希望他的作品“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他的事“也就完毕了”。不幸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纪念并未从人间消去,反而更强烈了,他的事仍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曲折地延伸。毋庸置疑,只要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痕迹没有消逝,鲁迅的批判、否定的思想文化体系就一定还闪烁着异彩,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和启迪。从这一点意义上讲,鲁迅还没有成为历史,他还在和我们一起继续书写着历史。
但我们还是希望鲁迅成为逝去的永久的历史,只有到那一天,我们才能说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才真正实现了,中华终于走向世界,世界也终于走向中华。
正因为如此,当现实需要我们在孔子和鲁迅之间作出选择时,我们宁可选择鲁迅,而不选择孔子,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鲁迅较之孔子,更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巨人,民族的灵魂和精英,其文化是名副其实的巨人文化,而孔子却还只是老百姓心目中的一个圣人,其文化还没有完全能够从圣人文化的光圈里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