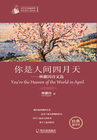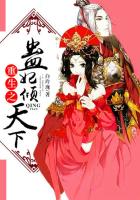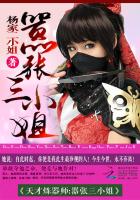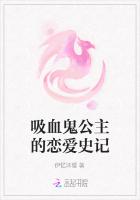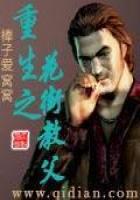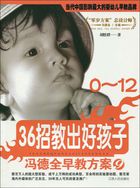从年龄文化的角度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生存发展的背景是一个以老年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向着一个老、中、青兼备的多元社会作巨大的转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注意到,由于不同的作家的生长环境、教育经历以及人生体验的不同,有的体现了较多的青年素质,有的则一开始就以中年人的姿态步入文坛,有的却以老人的形象出现,而这样的年龄差异又较多地受制于他们各自所在的区域文化环境。以区域文化的条块分割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年龄文化”特征,我们将不得不注目于四川。我们注意到,这里活跃着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更集中地聚集了中国现代作家中的“青春一族”。
一
无论是以发表处女作还是以成名的时间为限,四川作家都不愧为是“青春一族”。
巴金18岁发表处女作,26岁在《小说月报》连载《灭亡》,引起了文坛较大的反响。在类似年龄阶段起步成名的还有吴芳吉、康白情、林如稷、陈翔鹤、陈炜漠、李劼人、邵子南、周太玄、何其芳、方敬、陈敬容、邓均吾、沈起予、曹葆华、阳翰笙等,这一年龄阶段的人数最多;郭沫若发表处女作和成名的时间稍晚,28岁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30岁出版了划时代的诗集《女神》,类似的作家还有沙汀、艾芜、周文、罗淑、刘盛亚等。
但更能体现四川作家青春气息的还不在于生理的年龄(在其他区域内,类似的现代青年作家并不见得就少),重要的是他们常常富有青年式的思维、情感和心理。在关于四川作家的记录中,我们最容易读到这方面的描述。比如老舍眼中的郭沫若就“永远是那么天真、热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黄裳眼中的巴金“在谈天的时候,对一件事,一种社会现象,他常常会激动地发表意见,说得很多,往往说不下去了,就皱起眉用断续地‘真是,真是……’结束”。方敬笔下的陈翔鹤是“天真无邪,一如赤子”。沙汀、刘盛亚的创作是冷静的,但根据外省朋友的说法,他们本人却也“说话带感情,好激动”。
有意思的是,四川作家所发起或参与的社团名称也大多带有“新”、“新潮”、“创造”之类的意义,洋溢着一股浓郁的青春气息。诸如郭沫若、邓均吾、李初梨、阳翰笙、沈起予所在的创造社,李劼人、周太玄、王光祈所在的少年国学会,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王怡庵、李开先所在的浅草社,康白情所在的新潮社,赵景深所在的绿波社,曾孝谷所在的春柳社等等。偶然的“命名”是不是也暗含着某种必然的精神趋向呢?
如果说老年沉浸在过去,中年着眼于现实,那么青年则幻想着未来;如果说老年拥有成熟的思想,中年拥有务实的行动,那么情感则是青年的标志,青年凭着一腔热血去拥抱生活,享受生活,又运用幻想补偿人生的挫折。幻想与情感产生了诗,青春的诗情溢满了许多四川作家的心灵。现代四川流淌着一条诗之大河,从承先启后的白屋诗人吴芳吉到草堂文学社发起人叶伯和,从初期白话新诗的拓荒者康白情到划开一个时代的郭沫若,从中国式现代主义诗风的实践者何其芳、方敬、覃子豪与陈敬容到中国式革命诗歌的代表人柳倩、邵子南,还有邓均吾、曹葆华等等都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四川也诞生了大量优秀的小说、戏剧和散文,但不少的小说、戏剧和散文本身就是诗,是诗化的艺术。郭沫若的小说是诗,戏剧也是诗,林如稷、陈炜漠、陈翔鹤在“浅草”、“沉钟”时期的许多小说都以抒情为主,行动为辅,充满诗味,艾芜的小说《南行记》是一曲青春的抒情,何其芳、方敬、陈敬容的散文是诗化的散文,陈锉的小说和戏剧以浪漫性、传奇性相标榜,这也是一种诗的风格吧。丰富饱满的诗情,这是“青春一族”的重要的群体标识。
二
当我们细细领略现代四川作家那丰富的情感世界,我们发现,这些情感大体上有三个既相区别又有所联系的走向,这就是激情、温情和伤情。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人生内涵,但又都带着鲜明的“青春期”印迹,属于青年文化的表现。
激情文学的代表可以说是郭沫若与巴金。郭沫若涉足了多种文体,追求几经转变,诗歌(从《女神》、《星空》到《前茅》、《恢复》)也各有特色,但相对而言,奔放的激情还是他全部创作的底蕴。巴金反复向我们申说自己:“我不是一个冷静的作家,我在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时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
何其芳、方敬与陈敬容以他们的创作向我们展示了温情的魅力,所谓温情,就是内在的情感介于激愤与沉痛之间,既不过分亢奋热烈,也没有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的渊薮,它比较稳定,比较平和,每每能够从忧愁中见出乐趣,生发透明的希望。在抗战以前,何其芳“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美丽、安静、充满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诗和散文”。方敬则“喜守小室的明窗净几”,“有艺术的洁癖”。陈敬容痴迷于“深夜的幽客”、“木叶的足音”和“梦的暗蓝”。梦、辽远、美丽、温柔、宁静,成了他们创作共用的“意象”,这些意象织造起一个令人着迷的意趣盎然的境界,他们也都善于将忧愁与愉悦两种情感相互焊接,使之在特殊的组合当中彼此抵消,挫其凌厉,于是,最终走向了克制与中和、典雅与温软。
“浅草”、“沉钟”时期的林如稷、陈翔鹤、陈炜漠则把我们带人到阴惨惨的孤寂、索寞与感伤之中。他们为我们描述着青年人走投无路、灵魂飘荡的故事,或者感怀于人情的变故(陈翔鹤《悼》、《转变》),或者痛苦于目标的不定(陈翔鹤《不安定的灵魂》),或者受挫于理想与社会的冲突(陈翔鹤《写在冬空》、林如稷《流霰》、陈炜漠《轻雾》),故事似乎只是承载之物,承载着一颗颗受伤的心,承载着一道道带血的情感之流。
激情、温情和伤情正是一位刚刚踏上人生道路的青年人所最可能出现的三种心态与三种情感流向。
激情代表了青年人特有的胆识和勇气,他们一无所有,敢于面对一切,走向一切,所以豪迈奔放;温情代表了青年人对生存乐趣的不断撷取和对未来的默默的信念,他们愿意以自己美丽温柔的想象来补偿某些暂时的遗憾,因为未来的希望并不曾丧失;伤情则代表了青年人第一次独立应付现实世界的惶乱和不适,因为一时的茫然失措,他们有些晕头转向。豪情奔放的郭沫若、巴金在他们各自的创作中都体现出了一种对命运、社会和人生的“把定感”,对朝阳、对绿色、对春天的企盼则是何其芳等人的默默的情怀,而在林如稷、陈翔鹤和陈炜漠的感伤主义当中,稚嫩的气味是一嗅便知。他们抒情达志的依托都是一些刚出家门的学生或者刚出校门的青年,均没有独立应付生活的经验。陈翔鹤《悼》中的B先生害怕黑夜,不敢熄灯入睡,正像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秀姑所说:“怕……怕什么呢?又不是一个小孩子!”事实上B先生就是一个小孩子。
三
是什么力量将四川作家的青春期情感源源导出了呢?
我们探寻的目光首先落到了四川古代文学史上那同样蔚为壮观的诗情的河流中。古老的巴山蜀水没有为我们产生多少优秀的小说,却孕育了众多的诗人,从陈子昂、李白、薛涛、雍陶到花间词派,从苏舜钦、苏轼、韩驹到杨慎、李调元、张问陶,从举世仰慕的文人创作到名声远播的民间巴歌俚曲,众多的诗人生发着丰富浓郁的诗情,巴蜀由此而汇聚成为一个诗情丰盛的盆地,激情、温情和伤情都各有所出。陈子昂、李白、苏轼、苏舜钦、张、李调元的诗歌充分展示了豪情奔放、波澜壮阔的景象,而以西蜀词人为主体的《花间集》创作则“多为冷静之客观”,“而无热烈之感情及明显之个性”。可谓是巴蜀式温情主义的代表。而以巴渝民歌《竹枝》为代表,后来又吸引了不少文人仿制的作品,则充分体现了感伤主义的特质。
现代四川作家就生长在这样一个盛满了激情、温情与伤情的地域当中,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四川的小乡小镇,从小受到巴蜀民间文化的熏陶(包括何其芳、周文后来搜集过的山歌野唱),世易时移,当年让苏辙“掩泣”,令白居易生愁的“蛮儿巴女”之唱未必完全依旧,但其中的某些特征还是有所承传的。比如林如稷就曾在小说中描写一个乡场上的唱道情者,他的“自选曲目”都是戚切悲哀的:
差不多每夜最末了选唱的那一折,总是令人生广漠的悲感,觉得被歌声引入不快之境;有时把薛涛和琵琶行的事迹加以改窜和润色来唱,悲咽抑抑的调子,像春夜雨泣,秋晦叶啼,颤颤唧唧,若断若续,有时忽然从低音一变为高挺,慷慨嘹亮的放歌,如云间雁号峡谷猿啸,疾疾徐徐,时骤时急,这样连珠而下,刺着人酸鼻,几乎令各人回想到自己生活史上已往的悲哀处的断片……
由此等地域的此等抒情,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了林如稷的感伤主义了。
当然,更显著的还是对文人抒情传统的直接认同。李白式的激情和花间词派的温情已经成了现代作家自愿与不自愿的传统蒙学的一部分。比如,李白(还有苏轼)就是郭沫若一生钦慕不已的大诗人,对其诗作更是称颂再三,郭沫若把古典诗歌译为现代白话就是从对李白《日出入行》的处理开始的,这似乎表明,郭沫若照样能以一个现代人的心境去感受李白式的激情。何其芳则一度对《花间集》等晚唐五代的诗词人了迷:“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他又说:“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
在巴蜀地区源远流长的诗情的长河里,现代四川文学的情感追求找到了强大的根据。
四
但是,我认为,仅仅从特定地域的文学传统来解释现代作家的精神风貌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古老的传统与现代人毕竟是两种分隔开来的东西,前者之所以能够对后者发生影响,为后者所认同、所接受,一定是因为两者之间有某种跨越历史阻隔的精神上的同构性,而这种精神的同构又形成于某种更为深层的生存形态,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向下挖掘,剖析对现代作家尚有影响的属于巴蜀地域特色的生存形态。
我注意到,在巴蜀地域的生存形态中,有一个特征对巴蜀人的精神结构的影响始终至关重要,这就是巴蜀是一个远离儒家正统文化权威的“西僻之乡”,这里从来没有建立过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府,而源出齐鲁又广布于大江南北的儒家文化显然也在此积淀不深。这里缺少那种舍身取义以“正天下之风”的圣贤,巴蜀“名儒”如扬雄、谯周等都颇能审时度势,灵活善变。蜀学较之于北方的洛学也更能吸引道、释二家的思想。
这样的生存形态至少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巴蜀人的精神结构,其一是相对减轻了儒家文化的理性压力,其二是推动着巴蜀人的精神需要向着寻找实际生活情趣的一面发展,甚至为了寻找生活的意趣而置传统礼教的规范于不顾。这两个方面的特征又都可以总结为一种理性的“负轻”,也即是说,巴蜀人承受的正统的理性压力较轻。
文化的、理性的压力与感情的生长是一对矛盾着的力量,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北方具有更强的理性力量,它培养着人们的意志,削减着人们的情感,南方中国却反之。在情感发达的南方中国人之中,儒学理性压力更小的巴蜀人显得十分峻急和赤裸,特别是当这样的激情与某种巴蜀作家恃才傲物的叛逆意识一相配合,就更加势不可挡,无所顾忌。李白就是这样,难怪他被理所当然地当作了盛唐青春气象的代表。寻找和享受生活的乐趣,同样也是许多巴蜀文人的追求,即便是在晚唐五代烽烟四起的混乱中,生活在天府之国里的这拨人不思“扶危定倾,身任天下”,无意“经天纬地,建功立业”,也不“以修身为本”,反倒利用巴蜀丰富的出产尽情享受,一醉成欢。至于纵情使气,本来就是民间文学的特征,而在理性轻负的巴蜀地区,那种哀而有伤的“竹枝词”似乎也获得了特别的默许和放任。
在这种理性“负轻”的生存环境中诞生了我们的现代四川作家。较之于浙江、江苏及山东等省,近现代四川的儒家文化教育水准并不高,儒学气氛并不浓,从整体上看,这些作家受到的儒家文化的规范是不那么严格的。于是,这种传统理性的“负轻”感继续作用于现代四川作家的精神世界,一旦旧的文化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被动摇和摧毁,那么这一批负轻者就成了精神意义上的“青年”,他们负担较小,压力较轻,是“年轻”的文化人。现代四川文学的诗情奔涌的事实首先是这一批“年轻”的文化人以其独特心态选择的结果。
来自吴越之地的鲁迅因为自身文化积淀中无法挣脱的“毒气”、“鬼气”而彷徨踯躅,多重文化自相冲突的困境让他最终走向了审慎的现实主义,表现着鲜明的理性精神。鲁迅把炽热的情感包裹在强大的理性外壳之下,是为“死火”,这是传统理性压力作用于南方情感世界的一个结果。鲁迅是理性压力的“负重”者。与之不同,来自巴蜀的郭沫若似乎总能将本来不无矛盾冲突的文化遗产作自由的处理,令其互相比附、补充,比如把《庄子》、王阳明、“梵”和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拉到了一起,把先秦文化与“动”的“五四”精神相比附。这只能说明是一位传统的理性压力“负轻”者随心所欲的排列组合。当郭沫若走上文坛的时候,他并没有鲁迅那种深入骨髓的传统意识,所以也就没有更多地感到新旧多重文化的自我冲突,世界在“年轻”的郭沫若面前全新地展开,于是他豪情万丈。这样的激动似乎也用不着掩饰,用不着自律,它是奔放的,流光溢彩般迸射而出。这就是巴蜀式的激情。同样,巴金也很少谈及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他总是强调说:“在所有中国作家之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已经真正超脱了中国的传统,而是表明他也是一个“年轻”的文化人,是“年轻”人第一次向新鲜的异域世界撷取着文化之果,异域思潮炽热的火种点燃了巴金心中的热情。
何其芳、方敬和陈敬容当然从来也不是像花间词人一样的宴饮游乐之徒,不过,作为对儒家正统教育的“负轻”者,他们却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去寻找人生的意趣,憧憬心中的乐园,他们更有理由安于自足自慰的小天地而无须顾忌更多的“载道”的戒条。如果说花间词人还流露着一些兴亡之慨,多少显出一种青春将逝的隐忧,那么20世纪的何其芳、方敬和陈敬容却正当年轻,更有一种十足的青春气质,像每一个在清晨睁开眼睛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对世界的绚丽,那么好奇,那么饶有兴趣,那么想去尝试。
当然,青春又常常伴随情绪的起伏,反差很大。何其芳、方敬与陈敬容因为对儒家载道传统的“负轻”而陶然于个人精神的自足,因而可以默默地品味生活的温意。而对于另外一些既“负轻”传统理性,却又因为传统权威的倒塌未及采撷新的文化果实的人,情况又当如何呢?这个时候,便很可能因自身价值的匿乏而茫然无措、无所归依。“浅草”、“沉钟”时期的林如I、陈翔鹤、陈炜漠就是这样,我们称他们的情感特征为感伤主义,又不时将之与郁达夫的小说情调联系起来。其实,中国的感伤主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林如稷、陈翔鹤、陈炜漠的感伤主要在于他们各自的茫然无措,一种价值匮乏的飘荡感,正如陈翔鹤笔下的人物所说:“我自己实在是自有生以来,便不曾对某种东西沉醉过,我也不曾肯定过什么,也不想从事于某种生活。在这人世间,我知道我并不需要什么,我感觉我只是一个人。我完全是一个不定的魂。”在30年代初的小说《一个偶遇的故事》中也写到:“对于旧时所有的生活、道德、家庭、母性等等,都似乎已经失其信仰,而却又一时缺乏新的东西起来代替。于是只得在茫茫的人海中浮沉着,一任波涛澎湃,自己横冲直撞的,完全毫无出路。”
巴蜀式感伤主义与郁达夫感伤主义的区别恐怕也就在这里了。郁达夫的痛苦和孤独在于他自我的分裂,一方面是青春期的情欲冲动,一方面却又是深厚的道德自律以及在这种道德自律下的卑怯与病态。这种孤独、感伤源于作者主体结构中新旧多重文化的冲撞。我们说林如稷他们的感伤包含着传统的“负轻”感,而郁达夫的感伤恰恰在于传统的“负重”感。
文化意义上的“年轻”一辈,确乎在巴蜀。
这样,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说明古代巴蜀的文学传统对于现代四川作家的深刻影响了。可以说,首先是因为生存形态相似决定了古今作家在精神结构上共同的“负轻”现象,然后在这种精神同构的基础上,产生了文学追求的某些共鸣,于是影响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