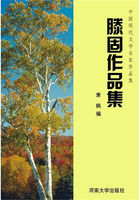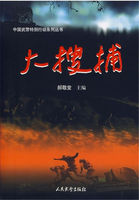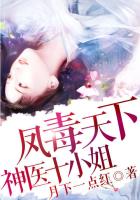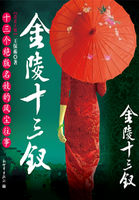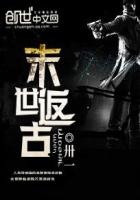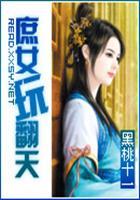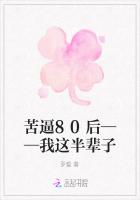我们要把固有的创造精神恢复,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精华,吸收古人的遗产,以期继往而开来。
——《文艺论集·一个宣言》
从出现在“五四”诗坛的那一天起,郭沫若就与众不同地公开宣布“要研究古代的精华,吸收古人的遗产”,将“开来”与“继往”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历数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等外来的影响,也照样一再重复着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孟浩然等中国古典诗人的“启蒙”意义,直到解放以后,诗人还坚持说“新诗在受外来的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原型”的意义在郭沫若那里特别地引入注目:它显然已经从无意识提炼为意识,从不自觉上升为自觉。
一
从郭沫若的自述来看,最投合他的情感,给他深远影响的中国古典诗人实在不少。不过,认真清理起来,又似乎分为两大类:一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二是以陶渊明、王维等人为代表的晋唐诗歌。他说:“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小时候就爱读他的作品。”还在旧体诗中满怀感情地吟叹:“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在多次的童年记述中,诗人又谈到了晋唐诗歌给他“莫大的兴会”,其中,又以陶渊明、王维为代表。比如在1936年关于《女神》、《星空》的创作谈里,郭沫若便说:“至于旧诗,我喜欢陶渊明、王维,他俩的诗有深度的透明,其感触如玉。李白写的诗,可以说只有平面的透明,而陶、王却有立体的透明。”以屈原为典型的诗歌形态和以陶渊明、王维为典型的诗歌形态就是郭沫若诗歌艺术的“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原型形态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原初阶段与成熟阶段,或者说是“自由”的阶段与“自觉”的阶段。
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由”形态。其基本的特征是:(1)自我与个性得到了较多的尊重。如《离骚》满篇流溢着诗人那恢宏壮丽的个人抱负,那“鹜鸟不群”的铮铮傲骨,开篇1句(今人断句),出现“我”(肤、吾、余等)就达6处之多,这在后世是难以想象的。(2)人不仅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还可以反过来调理、选择客观世界(自然与社会)。《离骚》的痛苦包含着屈原在选择生存环境时的两难,而他也尽可以“乘骥骥以驰骋”,“登九天抚彗星”,“逐龙唤凤,驱日赶月”,拥有无上的权威。(3)诗歌以意象的玄奇绚丽取胜,“弘博丽雅”,“奥雅宏深”。(4)全诗富有曲折、变化,显示出一种开阖倏忽的动态美。
陶渊明、王维所代表的晋唐诗歌属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自觉”形态。中国诗歌在这一时期由“自由”开始走向成熟,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大一统”、“超稳定”的产物,“大一统”、“超稳定”为中国文人提供了较先秦时代相对“坦荡”的出路,但却剥夺了那“纵横”驰骋的自由选择,中国文人被确定为一个严密系统中的有限的、微弱的个体,从属于“自我”的个性就这样日渐消融,或失散在了“社会”当中,或淡化在了“自然”当中,儒释道的成熟和它们之间的融洽共同影响着中国诗歌“自觉”形态的基本特征:(1)自我的消解,个性的淡化。(2)人接受着客观世界的调理,追求“人天合一”。(3)诗歌追求圆融、浑成的“意境”,“隐秀”是其新的美学取向。(4)全诗“恬淡无为”,显示出一种“宁静致远”的静态美。当然,不是所有的晋唐诗歌都是这样的冲淡平和,“以境取胜”,但是,陶、王的诗歌倾向却代表了中国诗文化在“自觉”时期最独特、影响最深远的抉择,尤其符合郭沫若当时的理解。
不言而喻,从思想到艺术,自由的诗和自觉的诗所给予郭沫若的“原型”启示都是各不相同的。那么,郭沫若又是如何看待这样的差别呢?屈原所代表的“先秦自由”向来为诗人所推崇,而陶王的“晋唐自觉”也同样契合着他的需要。诗人曾经比较了屈原与陶渊明这一对“极端对立的典型”,并且说:“我自己对于这两位诗人究竟偏于哪一位呢?也实在难说,照近年自己的述作上说来,自然,是关于屈原的多”;“然而……凡是对于老庄思想多少受过些感染的人,我相信对陶渊明与其诗,都是会起爱好的念头的。”“那冲淡的诗,实在是诗的一种主要的风格。”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表示:“我自己本来是喜欢冲淡的人,譬如陶诗颇合我的口味,而在唐诗中喜欢王维的绝句,这些都应该是属于冲淡的一类。”可见,郭沫若对这样的差别不以为然,他在“五四”时代的文化宽容精神也包括了对“差别”本身的宽容。
“自由”与“自觉”作为原型的意义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并在诗人主体意识的深处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
中国古典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是郭沫若用以迎纳、解释、接受西方诗潮的基础,正如庄子、王阳明是他认同西方“泛神论”的基础一样。中国古典诗文化的原型形态为时代精神所激活,在西方诗潮的冲击下生成了它的现代模式,这些现代模式往往包含着较多的现代性和西方化倾向,但追根究底,仍然是扭结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当中,是中国古典诗文化决定了郭沫若向西方世界选取什么和怎样选取。
“创造十年”结束后,郭沫若有过一段著名的自述:
我短短的作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泰戈尔式,第一段时期在“五四”以前,作的诗是崇尚清淡、简短,所留下的成绩极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这一段时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作的诗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热情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
尽管他的自我阐释借用了西方诗人的形象,几个阶段的划分也显得比较复杂,但是,一旦我们结合诗人的其他一些重要的自述加以分析,特别是深入到他的诗歌艺术世界之中,问题就比较清楚,比较“单纯”了,导致郭沫若诗歌如此三番五次的转折变化,其根本的原因仍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型”那里,是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的互相消长推动着诗人内在的精神需要发生着波动性的变化,而变化也不是漫无边际、难以捉摸的,或者是“自由”精神的增加,或者就是“自觉”意识的上升,总之,是自由与自觉的循环前进。
在《我的作诗经过》一文中,郭沫若将泰戈尔式的冲淡与陶、王等人的冲淡联系在一起,这说明,在他刚刚踏上诗歌创作道路之时,中国古典诗歌的“自觉”形态起着主要作用,这或许是每一个中国现代诗人都难以避免的诗歌启蒙时期吧,晋唐诗歌毕竟是中国现代诗人蒙学教育的最主要的内容。在郭沫若特有的“创造性误解”中,印度现代诗人泰戈尔创作的“冲淡”唤起了他“似曾相识”的亲近感,鼓励着他进行“中西结合”的选择。
“五四”时代,随着个性解放呼声的高涨,文学革命的蓬勃展开,惠特曼诗歌的传播,郭沫若那固有的“自由”基因又生长了起来。此时此刻,他所理解的“精赤裸裸的人性”,“同环境搏斗的”“动态的文化精神”以及“自我扩充”,“藐视一切权威的反抗精神”,都是先秦文化的“固有”表现,而屈原及其楚辞便是先秦文化的诗歌表述。所以说,郭沫若眼中的屈原多少有点自我投射的影响:
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文,在二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
《女神》就是郭沫若创造出来的“自由形态”的骚体,在《女神》之中,郭沫若塑造了一个个打倒偶像、崇尚创造、意志自由的“我”,他假借《湘累》里屈原的口说:“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女神》极力标举“自我”的地位,而客观世界则是“我”创造、吞噬和鞭策的对象,也是“我”的精神的外化。《湘累》有云:“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天狗》:“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日出》中的太阳成了奔腾生命的象征:“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你二十世纪底亚坡罗!/你也改乘摩托车吗?”与屈骚相类似,《女神》色彩绚丽,意象繁密,充满了波澜起伏的动态美。——包括奔突不息的形体运动和急剧变迁的思想的运动。如《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这是形体的运动;又如《凤凰涅槃》:“宇宙呀,宇宙,/你为什么存在?/你自从哪儿来?/你坐在哪儿在?/你是个有限大的空球?/你是个无限大的整块?/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这是思想的运动。
1921、1922年两年中,郭沫若多次回国,耳闻目睹的事实彻底摧毁了他复兴先秦文化精神的幻想,“哀哭我们堕落了的子孙,/哀哭我们堕落了的文化,/哀哭我们滔滔的青年。”(《星空》)为了舒散这些“深沉的苦闷”,诗人转向了《星空》时期,也就是他所自称的“歌德式”的创作。不过,所谓“热情失掉了,而成为韵文的游戏者”却并不是睿智而执著的歌德的本来面目,究其实,倒是中国诗歌“自觉”原型的第二次复活。如《雨后》:
初出的明星?
雨后的宇宙,
好像泪洗过的良心,
寂然幽静。
海上泛着银波,
天上还晕着烟云,
松原的青森!
平平的岸上,
渔舟一列地骈陈,
无人踪印。
有两三灯光,
在远远地岛上间明——
这很容易就让人想起了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自由”是中国诗人在社会动荡期个性展示的需要,“自觉”则是在社会稳定期聊以自慰的产物。有趣的是,这一历史规律也在郭沫若的身上反映了出来,留学海外的诗人,热情勃发,思维活跃,他很容易地举起了“自由”的旗帜;而一当他不得不面对中国社会稳固不变的现实时,“自由”就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想,于是,“自觉”的原型便悄悄地袭上心来。
但历史又给郭沫若提供了一次“自由”的机会。1923年以后,随着社会革命的发展,特别是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接触、认识,他那抑制着的,沉睡着的斗争欲、反抗欲获得了较先前更为强大的支撑,于是《前茅》、《恢复》问世了。“前茅”就是革命的、反抗的“前茅”,而“恢复”则是象征着诗人从“深沉的苦闷”中“复活”了坚强的意志,“要以彻底的态度洒尿”,“要以意志的力量拉屎”。(《恢复》)过去一般认为,《前茅》、《恢复》时期的郭沫若是对“从前深带个人主义色彩的想念”之反动,而诗人自己也明确地表示:“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两年之内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触,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总不免有几分偕妄。”其实,只要认真分析一下这一时期的诗歌,我们是不难透过那些“粗暴的喊叫”,见到诗人那怦怦跳动着的渴望自由、渴望自我展示的心,当他以所有受压迫者的代言人自居,大声疾呼,狂放不羁时,《女神》式的品格、《女神》式的诗学追求便清晰地呈现了出来:
革命家的榜样就在这粗俗的话中,
我要保持态度的彻底,意志的通红,
我的头颅就算被锯下又有甚么?
世间上决没有两面可套弦的弯弓。
——《恢复》
那么,继中国古典诗歌“自由”原型的第二次复活之后,“自觉”原型是不是也再一次地被激活了呢?从表面上看,包括抗战时期的《蝇蟾集》、《战声集》以及解放以后的《新华颂》、《潮集》、《骆驼集》、《东风集》等都洋溢着革命的激情,似与陶、王的“冲淡恬静”相去甚远,但是,考虑到诗人在这一时期,特别是解放以后的特殊地位,我们则可以肯定地认为,郭沫若已经没有可能再狂放不羁、“粗暴的喊叫”了,从理论上讲,他无疑将进入到“自觉”的形态。于是,我们不得不特别注意这样的事实:在这一时期,郭沫若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现象便是大量的旧体诗词的出现,而我们知道,中国古典诗歌正是在晋唐时代确立了自己的典型形式,“自觉”原型的第三次复活似乎首先就表现在诗歌艺术的形式之中;此外,我们还注意到,郭沫若的旧体诗词中,亦不时流出这样的句子:
山顶日当午,流溪一望中。时和风习习,气暖水溶溶,鸟道盘松岭,胶轮辗玉红。太空无片滓,四壁耸青峰。(《远眺》)
北海曾未此,岩前有旧题。洞天天外秀,福地地中奇。膏炬延游艇,葵羹解渴丝。流连不忍去,无怪日迟迟。(《游端州七星岩·游碧霞洞》)
芙蓉花正好,秋水满湖红。双艇现鱼跃,三杯待蟹烹,莺归余柳浪,雁过醒松风。樵舍句山在,伊人不可逢。(《访句山樵舍》)
居高官、忙政务,自然已不再是“冲淡”的时候了。但偶得闲暇,忘情于山水之间,那意识深处的传统文化原型便还会浮现出来。
总而言之,在郭沫若的诗歌艺术生涯中,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始终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发挥着至关紧要的作用。《星空》题序中郭沫若曾引用康德的名言说:“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结合郭沫若的创作实践来看,他显然是不无中国特色地把“星空”阐释为身外的客观世界,而把自我的自由意志、生存原则阐释为“心中的道德律”,前者诱惑诗人进入“自觉”,而后者则激发着人的“自由”。于是,中国诗歌原型的“自由”与“自觉”就的确是“刻刻常新”,“刻刻常增惊异与严肃之感”的。
三
在我们运用“自由”与“自觉”的原型意义,对郭沫若诗歌创作道路作了一个简略回顾之后,我认为有两点必须特别指出:
(1)所谓“自由”与“自觉”的循环生长只是我们对问题的比较粗糙的梗概性说明,实际上,除了这样有规律的演变之外,这两大原型形态的关系还要复杂得多,比如,在同一创作时期,“自由”与“自觉”也可能同时显示自己的力量,以致对郭沫若的诗歌创作造成一言难尽的影响。
(2)有趣的还在于,尽管郭沫若经历了这样曲折的诗风变化,尽管他也看到了“自由”原型与“自觉”原型给予自身的影响,但是显而易见,诗人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两大诗歌形态在他诗歌艺术中的特殊地位-它们的循环生长以及互相间的分歧、矛盾。
综合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认为,这已经清楚地表明,在郭沫若的精神结构中,“自由”与“自觉”又隐隐地呈现为一种彼此消长,相生相克的关系,生中有克,克中有生。
首先我们看“生中有克”。
“自由”与“自觉”共生于郭沫若诗歌发展的同一个时期,但是,由于它们在思想意义、艺术境界上的分歧、矛盾,郭沫若的诗歌因此而出现了若干诗学追求中的迷茫与瞀乱。这就是所谓的“克”。特别是当这两种原型都竭力在同一首诗中显示自己的意义时,其内在的裂痕就势不可免地裸露了出来。总的说来,“自由”唤起诗人的自我意识,要求对自我的“突现”,而“自觉”则极力消融自我意识,要求对自我实行“忘却”;“自由”让主体的形象与思想在诗中纵横,而“自觉”则一再陶醉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突现”与“忘却”、“纵横”与“陶醉”作为两种分离的诗歌艺术倾向竟也不时杂糅在一起,构成了郭沫若诗歌特有的“驳杂”特色。
如《凤凰涅槃》、西方的“菲尼克司”(Phoenix)“集香木自焚”,显然是自由意志的表现,诗中也“突现”了它的意志和思想,让它在咒天诅地中驰骋自己的感情,但是,当它“从死灰中更生”时,竟展示了这样的“自由”境象:
一切的一,和谐。
一的一切,和谐。
和谐便是你,和谐便是我。
和谐便是他,和谐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
不分你我他,不分自我与世界,所有的山川草木、飞禽走兽和人类都笼罩在一片“和谐”之中,这恰恰是中国诗文化“自觉”原型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如此突出“一”的哲学意义,也正是晋唐时代儒、道、释日渐“三教合一”的特征,只有在这个时候,老子的“道生一”,“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老子》),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佛学的“空”才被中国文人如此运转自如地把玩着。“自觉”最终掩盖了“自由”。
又如《雨中望湖》:
雨声这么大了,
湖水却染成一片粉红。
四周昏蒙的天
也都带着醉容
浴沐着的西子哟,
裸体的美哟!
我的身中……
这么不可言说的寒噤!
哦,来了几位写生的姑娘,
可是,unschoeh。
unschoeh意即不美丽、不漂亮。显然,郭沫若本来处于“自失”状态,“忘却”了自我,沉醉于西湖迷蒙的雨景当中。但是,其心未“死”,意识还在隐隐地蠕动,所以当异性一映入到他的眼帘,自我的欲望和思想就迸射了出来。“自由”完成对“自觉”的排挤。
类似的例子还有《梅花树下的醉歌》、《晚步》、《雪朝》等等。
不过,我们也没有必要格外夸大“自由”与“自觉”的矛盾对立关系。因为,它们虽有种种的分歧,但毕竟又同属于中国古典诗文化范畴内的两种原型,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自觉”形态与“自由”形态再有不同,也还是它辗转变迁的产物。以屈骚为代表的中国先秦诗歌再个性自由、自我突出,也终究不能与西方诗歌,尤其是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相提并论,先秦文化的“自由”和晋唐文化的“自觉”都有各自特殊的“中国特色”。
先秦文化的“自由”并没有取得西方式的绝对的、本体性的意义,它是相对的,又与个人的一系列特定的修养相联系,这些修养大体上包括了诸如宗法伦理、内圣外王的道德化人格、先贤遗训以及雏形的“修齐治平”等等内容,在屈骚中这些内涵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上,这已经就孕育了消解自我,人天合一的可能性(“天”有多重含义,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天理、国家民族之大义等等),为“自觉”时期中国诗文化的本质追求奠定了基础。相应地,晋唐文化的“自觉”又没有完全取消先秦式的“自由”,谈到个人的修养,包括陶渊明这样的诗人都无一例外地看重人伦道德,崇尚先贤风范,晋唐诗人依然“自由”地表述着自我的思想情感、只不过,他们是将更多的“自我之外”的精神因素(自然生命或者民族责任)内化为个人的思想情感,是“自觉”中的、“自由”。
自由原型和自觉原型在深层结构上的这种一致性,自然就被郭沫若领悟和接受着,并由此形成了郭沫若诗学追求“多中见一”、“杂中有纯”的特色,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克中有生”。“克中有生”是我们窥视郭沫若诗歌深层精神的一把钥匙。
自《女神》以降,郭沫若的“自由”追求深受着屈骚精神的影响:“自由”不是纯个体意义的,当然更不是绝对的,它总是以民族的救亡图存为指归。“不愿久偷生,但愿轰烈死。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棠棣之花》)自我也并不是无所顾忌地追逐个人的利益和幸福,他常常以“济世者”自居,又站在“济世者”的道德立场上去观察世界和他人,这样,“匪徒”都成了献身社会的仁人志士(《匪徒颂》),而劳动人民也成了怜惜、同情的对象,(《辍了课的第一点钟里》、《地球,我的母亲》、《雷峰塔下·其一》)郭沫若从来不开掘自我的内在精神状态,从来不对人的精神自由提出更复杂、更细致也更恢宏的认识,也较少表现自我与自由在现存世界面临的种种苦况与艰难,而这些又都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所必须解决的问题。郭沫若更习惯于在中国原型形态的定义上来呈现“自由”,来“呼应”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这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即当诗人要如西方诗人式的竭力突出“自我”、挥洒“自由”时,他便更显得有些中气不足,内在的空虚暴露了出来。
《天狗》可能是郭沫若最狂放自由的作品,但是,从吞噬宇宙到吞噬自我,“天狗”的精神恰恰是混乱的、迷茫的,缺乏真正的震撼人心的力度。有的时候,诗人为了表现自身的“创造力量”,无休止地将中外文化的精华罗列起来、堆积起来:“我唤起周代的雅伯,/我唤起楚国的骚豪,/我唤起唐世的诗宗,/我唤起元室的词曹,/作《吠陀》的印度古人哟!/作《神曲》的但丁哟!/作《失乐园》的米尔顿哟!/作《浮士德》悲剧的歌德哟!”(《创造者》)但一个创造者究竟应当有什么样的气魄呢,我们所见有限。到了《前茅》、《恢复》时期,这种自由与抗争的空洞性就更加明显了。有时候,连诗人自己也深有体会:“我是诗,这便是我宣言,/我的阶级是属于无产,/不过我觉得还软弱了一点,/我应该要经过爆烈一番。//这怕是我才恢复不久,/我的气魄总没有以前雄厚。/我希望我总有一天,/我要和暴风一样怒吼。”(《诗的宣言》)
自我意识的收缩,自由精神的空疏这也决定了郭沫若对待客观世界的态度。我们看到,尽管诗人面对高山大海时常升腾起对生命的颂赞,时常唤起一种激动人心的崇高体验,但是,他却始终把自己放在了这么一个“被感染”、“被召唤”的位置。
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人与自然相搏斗、相撞击的景观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表现。从这个逻辑出发,当诗人的“自我”和“自由”在实践中被进一步地削删、稀释之后,客观世界便理所当然地显出一些威严恐惧的气象,给诗人以压迫,以震慑:“啊,我怕见那黑沉沉的山影,/那好像童话中的巨人!/那是不可抵抗的……”(《灯台》)诗人在客观世界的风暴中沉浮,久而久之,他终于疲倦了,衰弱了:“一路滔滔不尽的浊潮/把我冲荡到海里来了。”“滔滔的浊浪/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我要儿时候/才能恢复得我清明哟?”(《黄海中的哀歌》)
当人在客观世界面前感叹自身力量的弱小,而又并没有获得更强劲更坚韧的支持时,“天人合一”的理想便诞生了。在对民族大义的铿锵激动中,在“澄淡精致”的大自然中,我们那疲弱的心灵才找到了最踏实更妥帖的依托。于是,中国诗歌便转向了“自觉”形态。“自由”到“自觉”就这样实现了它的内在的过渡,“自由”与“自觉”的循环便是以此为基点、为轴心。
在《星空·孤竹君之二子》的“幕前序话”里,郭沫若阐发了他关于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天地间没有绝对的新,也没有绝对的旧。一切新旧今古等等文字,只是相对的,假定的,不能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在诗歌创作中,他假借了中国传统诗文化的“自由”原型与“自觉”原型,试图吹进现代生命的色彩,当然,郭沫若又还未曾料到,“古人”并没有僵死,更不都是“骸骨”,它也可能对今天的新生命产生出鞭辟人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