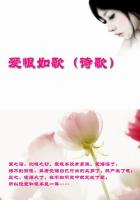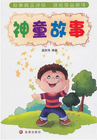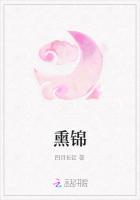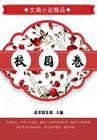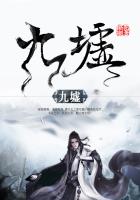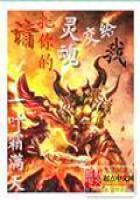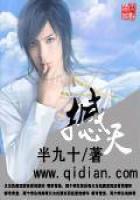继《蜕变》之后,曹禺于1940年深秋创作了《北京人》。1941年12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了单行本。
在曹禺的剧作中,恐怕再没有比《北京人》受到误解的批评更多了。这些误解的批评意见涉及对作家创作思想、艺术风格、基调的准确理解和评价。有些意见在抗战期间就有影响,而全国解放后还在若干文学史著作中流传着。应当说,对《北京人》的研究远不及《雷雨》、《日出》那么广泛而深入,似乎它像蒙上一层灰尘的艺术明珠,需要拂去那些历史残留的灰尘,才能恢复其璀璨的光辉。
当作家满腔热忱反映抗战的现实,写出了《蜕变》,忽而又掉转笔锋去描写抗战前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家庭时,就使得一些评论家感到迷惑不解了。于是便有人说,《北京人》是作家“于失望之余,悲哀心情的表现”,是作家唱出的一曲低回婉转的挽歌。“他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非崩溃不可,但是他却爱恋那种势必随着封建社会死亡的道德与感情,他低回婉转地不忍割舍,好像对于行将没落的夕阳一样。在《北京人》他唱出了他的挽歌,是又幽静、悲哀的呀!然而他却无法留住那行将死灭的道德与情感,跟‘无计留春住’,是同样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些,无疑是把《北京人》当做曹禺为痛惜本阶级的灭亡而写出的悲哀文字了。有人还认为,作家写的是一部缠绵悱恻的悲剧,“当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感到不那么乐观的时候,他的写作便转换了方向。他送给了我们《北京人》的悲剧”。皮相的观察自然导致误解的批评;而不作过细的艺术分析,也不可能深入地领略剧情的深刻含意。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北京人》首次在重庆公演之后,它不但受到观众的好评,而且得到《新华日报》的热情肯定。《新华日报》最早刊登了柳亚子先生的《〈北京人〉礼赞》,这是一篇用诗歌写的剧评。他对《北京人》的主题作了富于诗意的概括和发挥。
旧社会,已崩溃;新世界,要起来!只有你,伟大的北京人呀,继承着祖宗的光荣,还展开着时代的未来。
破碎的大家庭,已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摧残!老耄的白发翁,还依恋着古旧的棺材!长舌的哲妇,自杀的懦夫,都表现着旧社会的不才!只有伟大的北京人呀!一分力,一分光,正胚胎着时代的未来!
多情的小姐,洗净她过去的悲哀!被压迫小媳妇儿,冲破了礼教的范围!跟着你,伟大的北京人呀!指点着光明的前路,好走向时代的未来!柳亚子:《〈北京人〉礼赞》,1941年12月3日《新华日报》。
继之,又发表了茜萍的《关于〈北京人〉》,这篇文章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北京人》的创作意义。它似乎是针对那种“在抗战期间不应写这类与抗战无关的剧本”的“抗战八股式的批评”而发的,因此,也可以说它是一篇为《北京人》辩诬的文字。她说:“抗战为着什么?是为着打走敌人,为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社会。但是为着建立新社会,就不能不对于旧的社会作深切的研究,明确的认识,尖锐的暴露,坚决的攻击,这才能说到正确的切实的改造,把旧社会送到曾老太爷漆了几十年的楠木棺材里去,这样,我们也才能获得抗战胜利的真实果实。”她还指出,像《北京人》这样的剧作,也能扫除“阻碍抗战进步”的“旧社会的生活、习惯、意识形态”等传统的东西,也可以“唤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茜萍:《关于〈北京人〉》,1942年2月6日《新华日报》。。这些批评体现着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也体现着党对曹禺创作的关怀、支持和爱护。当时茅盾也撰文指出:“绝不能低估《北京人》的价值,低估它的社会意义。”茅盾:《读〈北京人〉》,1942年4月27日《解放日报》。但是,这些中肯的意见未能为后来文学史家所重视,而把一些误解的批评意见作为依据了。
在我们看来,《北京人》是曹禺解放前戏剧创作的高峰,无论它的思想还是艺术都标志着曹禺剧作的最高成就。他的创作经过斗争风雨的磨炼,思想更加沉实,艺术也更为成熟了。他不但把他的剧作风格锤炼得更加隽永含蓄,而且在探索话剧的民族化群众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使《北京人》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特色。而这些,正是我们准备着重探讨的课题。
一是悲剧还是喜剧
曹禺写作《北京人》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情,它是否是“失望之余”的作品?另外,《北京人》究竟是一部悲剧还是喜剧?这些是值得弄清的问题。它关系到对《北京人》的主题思想、戏剧基调和艺术风格的准确评价,也关系到对曹禺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深入探讨和理解。当有人把《北京人》看做是作家“悲哀心情的表现”,或者把它作为一部悲剧来评价时,他们就像鲁迅批评的那样,犯了“就诗论诗”的毛病。既不能“顾及全篇”、“顾及作者的全人”,又不能“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而在艺术上,更不能体味作家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匠心。
一个作家的创作道路具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它又不能不受时代的制约和限制。作家对时代现实的态度和感受不能不反映到创作上来。曹禺的创作道路是不平坦的。作为一个正直的进步的作家,他在整个民族的大动荡的斗争旋涡中,在探索真理探求艺术的道路上勇敢地前进。如我们已经揭示出来的,由《雷雨》、《日出》的创作表现出作家敢于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带来他现实主义创作蓬勃发展的势头,经过了《原野》的探索,当他还未来得及深入总结时,就迎来了全民抗战的形势。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关头,他把他的全部热情奉献给这伟大的抗战事业,《黑字二十八》、《蜕变》都是他爱国热血沸涌的产儿。可以说,他是以空前未有的政治热情从事创作的,他把对胜利的渴望,民族的“蜕变”化为炙人的理想温热。尽管他目睹国统区的黑暗腐败,仍以他真挚的乐观写出了他“蜕变”的渴望。按理说,他似乎应当以更加充沛的抗战热忱去反映抗战时期的斗争生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却写出了《北京人》。乍看起来,几乎使人难以相信这是在抗战时期写出的作品,也几乎嗅不出抗战炮火的硝烟味。现象往往是迷惑人的,谁要是潜心地观察和深入地思索,就会发现在《北京人》的“哀静”的表层下仍然激荡着曹禺那种热情激流,蕴蓄着作家动人的理想温热。在他对抗战前现实生活的描绘中,深刻烙印着他对抗战现实的严肃的思索,他想得更深更远些了。他并没有“转换方向”,而是更坚实地沿着他的现实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前进了。他送给人们的不是一部悲剧,而是一部具有浓烈抒情色彩的喜剧。
曹禺说,“《北京人》可能是喜剧,不是悲剧。里面有些人物也是喜剧的,应该让观众老笑。在生活里,老子死了,是悲剧;但如果处理成为舞台上的喜剧的话,台上在哭老子,观众也是会笑的”张葆莘:《曹禺同志谈剧作》,《文艺报》1957年第2期。。我们认为,这是打开《北京人》思想和艺术底蕴的一把钥匙,作家自己揭示了这部作品喜剧的本质。
当一个作家要写出一部现实主义的喜剧时,它意味着作家对现实的喜剧感受是格外锐敏而深刻了。在吃人的社会中,当作家充满对吃人现实的悲剧理解,自然,也能写出伟大的悲剧;而作家终于发现了吃人现实的喜剧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往往说明着作家高昂的斗志和睿智的见地。曹禺终于写出一部喜剧,归根结底是喜剧现实的产儿。
抗战的现实是变得越来越具有讽刺意味了。
从《蜕变》到《北京人》,虽然其间只隔了一年时间,但这一年间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经历了一个从抗战初期的高潮陡然跌落到低潮的阶段。曾几何时,它就使得人们由希望变成失望,由热情而变得沮丧,而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现实是一幅极度令人愤慨的讽刺图画:一方面是共产党八路军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绝大部分;一方面则是蒋介石暗地里背弃抗日、民主的诺言,消极抗日,积极制造反共摩擦,暗中策划着投降活动。但是,蒋介石却又打着“抗战”的招牌,假统一之名,行独裁之实,推行其“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专制主义,“反共、限共、溶共”的把戏愈演愈烈。在整个国统区,特务横行,屠杀共产党人,囚禁爱国人士。贪官污吏形同虎狼,乘国难大发其财,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这些冷酷的现实,不但充分暴露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而且暴露了黑暗的社会制度已经发展到腐朽垂死的阶段。这种极度讽刺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作家的沉思。
伴随着政治上的反动而来的,则是对进步文化事业也极尽摧残迫害之能事。阳翰笙曾指出这一时期国民党对进步戏剧事业的压迫情况,他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各级特务机关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却对我们随时随地在行动上予以妨害,在工作上进行破坏,从而解散剧团,逮捕监禁,枪杀活埋,无所不用其极。”阳翰笙:《国统区进步的戏剧电影运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页256。曹禺早已身受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之害。《蜕变》演出时连蒋介石都出面干涉了。当时,国民党一位宣传大员找到曹禺说:“委员长看过这个戏了,有几个地方没有看懂,请你解释一下。”一个作家写了一个抗战的剧本,竟使得蒋介石亲自发难,可见文网周纳,逼得人连抗战戏也不能写了。这种迫害干涉,并没有使曹禺放下他战斗的笔。他把创作的视野转向抗战前的现实,这既是被迫无奈的选择,但又是一个具有深知卓见的恰当的决定。他自然不会再有热情去写他的“蜕变”愿望,因为事实已粉碎了他“过分的乐观”,但是他也没有对祖国的前途产生失望。他的心情不是变得悲哀了,而是从事实的教训中,更清楚地看到了希望在什么地方。于是,他选择了他熟悉的生活来写,而把他对现实的喜剧感受熔铸于一个大家庭的生活描绘之中。他把矛头对准那像棺材一样腐朽的社会制度,挖开眼前反动腐朽统治的根基;同时,把真正的希望——对革命的希望真切地展示出来。他的一位学生回忆了作家创作《北京人》时的心情:
大概是在1940年的深秋,在四川江安靠近古旧城墙边上的一幢房子里,曹禺同志写作了《北京人》,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正在作他的学生。曹禺同志也不过三十岁。他正热爱着契诃夫,感到时代的苦闷,也憧憬着时代的未来。但他的思想已经不仅仅是停滞在憧憬里,而且看到了和懂得了北方为着幸福生活斗争的人们。所以他也热爱我们那一群青年人。我们整天生活在一起,他把《北京人》剧本,写好一段读一段给我们听。我记得江安的夜晚没有电灯,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铺满了稿纸,窗外是梧桐秋雨,曹禺同志以最真挚的心情叙说着愫方的善良,他回忆着充满生命力的古代人类向自然的斗争,对当时的现实斗争充满了希望。方琯德:《看〈北京人〉忆旧感新》,《戏剧报》1957年第13期。
《北京人》是一部对现实斗争充满着希望的作品。尽管曹禺说,他写《北京人》时,“还根本不懂得革命”,但是“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曹禺:《曹禺选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这点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他把他所描写的生活同革命联系起来,无论是观察现实和描写希望就带来新的因素和新的特色。而我们把《北京人》的喜剧特质,是作为他现实主义发展的新特点加以看待的。
确实,《北京人》是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悲剧的。它的抒情气氛是太浓郁了,这种深沉的诗意抒情往往遮掩着它的喜剧性,它确实也有着悲剧的成分,有时,其中弹出的那种凄凉的调子和类似悲剧的场面,也容易给人以错觉。别林斯基曾说:“喜剧性、幽默、讥刺,不是大家都能懂得的,一切激起笑声的东西,大多数人通常总认为比激起高扬的喜悦来的东西低。直接而肯定地说出的概念,总比其中包含着和字面相反的意义的概念,容易被人了解些。喜剧性是文明之花,是发展了的社会性的果实。要懂得喜剧性,就必须站在教养的高级阶段上。”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页125。
一般说来,人们对现实的悲剧感受比较容易些,而喜剧性却潜藏在现实深处,而《北京人》正是把隐蔽于悲剧现象后面的喜剧性发现出来;那么,作家就把他的现实主义的戏剧艺术推向一个更加深化的新境界。
很久以来,人们习惯把曹禺作为一个善于创作悲剧的作家来研究,而往往忽视了他对喜剧的兴趣和追求。可以说,《北京人》也是作家长期以来探索喜剧艺术的必然结果。
还在《日出》写作时,就表现了作家杰出的喜剧才能和强烈的喜剧兴奋。当时,他就沉醉于契诃夫的戏剧艺术之中,深深地为《三姊妹》的艺术感动着。正如高尔基所说,契诃夫的戏剧“创造了一种完全独创的剧本类型——抒情喜剧”。曹禺崇拜着契诃夫,并要“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他所追求的正是契诃夫独创的这种抒情戏剧的风格。正如我们指出的,在《日出》中渗透着契诃夫戏剧的影响,特别是在悲剧和喜剧的交织渗透上,颇得契诃夫抒情喜剧的启示,但是,他没有彻底贯彻下来,最后还是完成了一部悲剧。而从此契诃夫的戏剧艺术,如作家所承认的,“抓牢了我的魂魄”,成为他十分向往的美学境界。《蜕变》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作家的喜剧激情,他运用讽刺的手法活画出那些腐朽分子的嘴脸。夏衍甚至说,《蜕变》的第一、二幕“有点像《钦差大臣》”,“在布局上,可以说有点像吧”夏衍:《观〈蜕变〉》,转引自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编:《现代文学参考资料》。。但是,因为他毕竟要写出“‘蜕’旧‘变’新的新气象”,也不能把这种讽刺的激情贯穿全剧。
需要提及的是,作家还改编过一个独幕剧《正在想》。这个戏有人把他当做曹禺的创作了,其实作家在篇末注明了,它是“根据Niggli的TheRedVelvetGoad大意重写”。它虽然是一个改编的剧本,却表现了作家日益增长的喜剧激情。有人说:“曹禺有将近五年不曾写作了,他很想改变自己与现实的关系,可能《正在想》所反映的正是作者此时自嘲的心境吧。”这个说法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个戏仍然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它写一个变戏法的马家班,生意萧条,观众冷落,为了追求时髦便改演话剧,于是就闹出许多笑话。对于欺压人民作霸一方的保甲长作了辛辣的嘲讽,对于那些流荡在生活底层的卖艺人,于善意的笑声里刻画出他们的辛酸和不幸。它以喜剧形式展示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世态一角,内中透露出作家的激愤和感慨。
当我们回顾了作家的喜剧追求,就会对作家写出《北京人》这样的抒情喜剧不再感到是偶然的了,它是作家不断积累起来的对现实的喜剧感受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