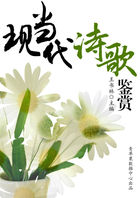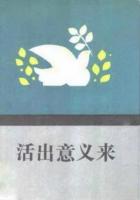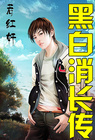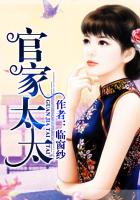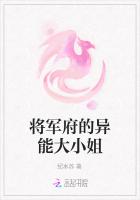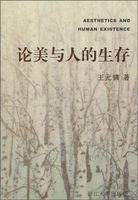李贽终于趁着剃头师傅转身时,拿起那把剃刀,顺手从自己颈项间一抹而过。顷刻间,血喷如射,四处飞溅,那位待诏以及在场的狱卒,对这意想不到的突然事故,简直来不及反应,都吓呆了干站在那里。
他,神色不变,还是那副淡淡的,甚至有一点讥诮意味的笑容。
这自然是隔了数百年后的臆测,但也是这位老人势所必然的表情。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活得实在不能再活的时候,大致可出现两类情况,一类是自杀,宁折不弯,自杀是需要大勇气的行为,能够下决心自杀者,通常不是懦夫;一类是不自杀,好死不如赖活着,趴在地下当狗、当狗屎、当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都可以,就是不肯结果自己的生命。
我属于后者,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里,逼得我曾经尝试过自杀。那是在山区,悬崖峭壁,只要脚一歪,就是粉身碎骨的结果。我怯懦了,因为我见过山区老乡用这种办法处置老牛。耕牛是不许宰杀的,然而这头牛太老了,而乡亲们又久久没见过荤腥,于是,队长叫来一个地富子弟,让他干这件事,万一上面责怪下来,好拿他去顶罪。即使老牛,它也不想死,当它大半个身子翻滚下去,前面两条腿还拼命攀住岩,那求生的欲望,让我益发感到自己弄死自己之艰难。想到老牛怖死的一霎那,算了,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当任人践踏的狗。
李贽敢自杀,我佩服他,虽然他不是一个十分的强人,但是,他敢于对那些“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东西说不;对“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鄙儒”、“迂儒”、“腐儒”、“俗儒”们说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绝对真理说不;对《六经》、《论语》、《孟子》等等经典著作说不;对体制内一切认为正常的游戏规则说不……这种反叛精神,在只许点头称是,而不准抬头说不的封建社会里,实在是极有勇气的行为。翻开中国文化史,如李贽般逆潮流者,简直寥若晨星,如李贽般唱反调者,更是空谷足音,这恐怕就是封建社会得以迁延数千年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士,也就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骨头里过分缺钙!
李贽不该到北京来的,但他的性格决定他非来不可。还未进朝阳门,只是在通州,就被告到诏狱里去。理由很简单,李贽是祸水,“敢倡乱道,惑世诬民”,在麻城两次被州抚勒逐出境,现在此人已经到了通州,天哪!“通州离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告御状者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坏蛋一个,正是李贽咒骂了一辈子的伪道学、伪君子之类。其实,李贽早几年就对他朋友山西主考汪可受说过:“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这一状告得他正中下怀,但很遗憾,没造成一点轰动效应。相反,无声无息,不死不活,于是,他决定自杀。
他学问当然很大,但对于切腹割腕自缢饮鸩之道,似乎缺乏研究,也许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尤其明代)宁肯撅起屁股挨板子,鲜有决绝而自杀者。于是,无章可循的他,选择这种割脖子的方法,来结束自己生命,看来是平素里他太太杀鸡杀鸭,给他的启示了。虽然未能一刀毕命,但自杀是成功了,他很欣慰,无论如何,他要最后一次让国人震惊,让历史震惊,果然也达到了目的。可以想象,他这一刀下去,痛苦其次,快感是第一位的。
这是发生在公元1602年(万历三十年)春天的北京的事情。这年,李卓吾已经75岁。如此高龄的自刎者,若放在当代,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老夫子在死亡线上折腾了两天以后,终于因为喉管被割的缘故,在无法言语的难堪沉默中,与世长辞。呜乎,大师远行,凡尘两隔,再也听不到他那闽南口音的刺耳之声了。农历三月的北京,那应该是一个风沙飞扬的天气,应该是一个天昏地暗的日子。我想,在这个众人都不敢说“不”的国度里,这是送别大师的最好场景。
李贽之死,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别人,包括爱他的,敬他的;恨他的,怕他的,也是一个解脱。说实在的,大家都感到如释重负的轻松。卓吾老夫子这一生,尤其到晚年,仍给自己订下了太多的目标,多到了闹人的程度,实在是不敢恭维的;其实,这些在他古稀之年还要去奋斗、去树立的东西,只不过是他数十年来所作所为的平面延伸,同类项的不断反复罢了,对于他,对于别人,已不再具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意义。
有一支小提琴曲,叫《无穷动》,听一听那休想宁静的旋律,对于了解李贽,也许会有帮助。闹,或太闹,是中国文人一旦有点名声以后,便患有的永远治愈不了的痼疾。
古人云:强弩之末,难穿鲁缟,谁都会有这一天的。可李贽犹不收弓,犹以为尚能百步穿杨,犹拉开架子跃跃欲试,这是中外古今所有大人物难以逃脱的最后悲哀。观众对这类戏演完了仍不肯卸妆的角色,只有悲悯,而不同情。因为你不能老在舞台中央,占着茅坑不拉屎。李贽应该明白,你就是你,你已经是你。你辞官,你落发,你遣妻送女,你成为云游四方的不僧不道的老单身汉,早就定型了。折腾,是李贽,不折腾,还是李贽;闹,不会多,不闹,也不会少。
但是,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名声,有时候比金钱,更能弄得人魂牵梦萦,颠三倒四。李贽这一生,之所以远离家乡,之所以妻死不娶,之所以过着这种仰鼻息于豪门、吃白食于官衙的日子,议论讲学,授徒交友,著书立说,招摇过世,就是保持这种体制外的领袖群伦的地位,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做一个在世圣人。
凡人物(或其实算不得人物,只是自我感觉也是个人物),都会程度轻重地患这种病。一旦发现居然人五人六了,从此,就不做那个本色的自己,而偏要做众人眼中的那个人物了。
李温陵先生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个尤其爱闹的人,已经闹得刹不住闸,必须按这种活得很累的生存方式闹到底。汤显祖就埋怨过他:老先生啊!“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你老人家干吗一定要闹到天子脚下呢?但剧作家哪了解尊师是绝不怕闹大的底里,他一定要随马经纶御史到通县来,也是觉得在麻阳,在南京,闹动的震撼度不够大。所以,逮捕令一下,他好像求之不得,连忙招呼下人抬门板过来,他躺在上面,让送到京城。谁知审判长不把他当回事,“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予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袁中道《李温陵传》)
听说要将他遣返原籍,李贽觉得这场真是该演完了。他一生两畏,一畏回乡,二畏回家,是绝对行不得的,于是,决定自杀,而且采用了近乎“行为艺术”的死法在内,也透出他必闹到别人目瞪口呆的风格。
1602年春天的北京城,那肆虐的风沙,显然比现在的状况还要糟得多。最虔信李贽的公安三袁之一的袁小修,写过一篇《游高梁桥记》,讲到与其兄袁中郎同去西直门外踏青,被沙尘暴挡回来的狼狈,“坐至丙夜,口中含沙尚砾砾”,可见风沙之烈,也可见彼时的中国人,尚无牙刷和刷牙这一说。就在同样的三月天,在通州北门外的迎福寺边,人们冒着扑面噎口的扬尘,草草地葬送走了李贽。“行年七十六,死无一棺”(明陶望龄《歇庵集》),这倒也符合卓吾老夫子的一贯精神。
沙尘能将元大都的遗址,埋在地下不见踪影许多年,但是,掩埋李贽尸骸的那块黄土,却遮挡不住他那“逆潮流”的精神。争议一直伴随着他的名字,讨论到明末,讨论到清初,褒者有之,贬者有之,官方封杀,民间传播,死了以后还要让人不安生,说明李卓吾一生没有白闹。
明末清初,一些在野的大学问家,对李贽的行径持反感态度。如顾炎武:“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过于李贽。”如王夫之:“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稍后一点,在朝的王士禛也同样:“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其言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更甭说编纂《四库全书》和《明史》的纪晓岚和张廷玉了,对李贽简直近乎唾弃了。
其实,即使如李贽最看重,最推许的,甚至向其请求“公能容我作一老门生乎”的焦竑,也对这位闹得十分厉害的老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当他考中一甲进士第一名,任翰林院编修,李贽很想依附于他,他以“身心俱不得闲”婉拒。自作多情的李贽在他《焚书》中,收录了那么多的《与焦弱侯书》,其中不乏肉麻吹捧,但焦竑的《澹园集》和《澹园续集》,却绝不保留一封他给李贽的书信,显然是有意剔除掉的。他的《玉堂从话》一书,虽记万历以前的文人雅事,但并非只字不提同时代人,然而找不到李贽的名字。看来,李贽的闹,对持道统观念的文人学者来说,颇有点格格不入。
想不到十年文革期间,老先生又给挖出来热闹了一场。谁让他四百年前,抬举那位名叫武则天的女人呢?于是,被四百年后的另一位女人,引为青衫知己。这次,李贽以“高级篾片”的角色,扮了一次三花脸,很不体面。一时间,他的《藏书》、《焚书》,重印出来,居然把汪曾祺先生的《沙家浜》,浩然先生的《艳阳天》挤到一边去,堂堂陈列于书店柜台正中为热销品。好在评法批儒,雨过地皮湿地过去,老先生与那些泛起的沉渣,很快沉落下去,总算没有请到写作组当高参,万幸万幸。
李卓吾一生,以割脖子为代价,不屈不挠“逆潮流”到底,说“不”到底。作为中国文人中特别能闹者,总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在世圣人者,多少患有一点自大狂者的这一种人,是值得研究和总结的对象。当然,这类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但如今这等活“圣人”的肚皮里,除了一副好下水和良好的自我感觉外,别无长物。环视当下文坛,草包实在太多,菜鸟尤其不少,像李贽这样有学问的自以为是的圣人,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咧!
李贽,福建晋江人,原姓林,有色目人血统,到他祖父一代,已完全汉化。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乡试及第,也就是俗称的中了举。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离开老家,携家眷到河南辉县任教谕一职,约相当于县教育局的督学。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迁南京国子监教官,大概是个什么教研室主任之流,也是个闲差。因为明朝自永乐迁都北京,不好擅废他老爹朱元璋的首都,便象征性地在南京建立了一个缩微的政府机构,养一批闲官。
所以,李贽自及第以后,不算怎么走运,先是丁父忧,后是丁祖父忧,忙于奔丧,即使得到一官半职,也是在清水衙门坐冷板凳,仕途很不顺畅。直到1576年,才调任云南姚安(即前不久发生地震的地区)当知府,这才有一点俸禄外的灰色收入,使口袋稍有充盈之感。此公熬煎了24年,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等得太久太久”,实在是相当的不耐烦。换个别人,也许认命,但他,很不愿意如此按部就班,从体制内循序渐进上去。他肯定会骂娘的,“熬到出头之日,还不得到驴年马月?”所以,他的“逆潮流”的思想,和说“不”的行动,一是他的天性狂狷所致,二也是一生遭际所赐。
在这里,倒无妨参照《红与黑》里的那个于连,重温斯汤达笔下这个外省青年的心路历程,也许对四百年前走出泉州古城的李贽,有所了解。那个木匠的儿子,从外省小镇来到首善之区巴黎,能够站稳脚跟,大展宏图,能够不择手段,达到目的,能够无所不为,下作行事,能够蚕食鲸吞,捞取一切,能够寡廉鲜耻,背叛出卖,能够声色犬马,与那些贵妇名媛上床。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没有揭竿起义,没有明火执杖,没有革命宣言,也没有推翻政权,而是穿着燕尾服,戴着白手套,含情脉脉,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谦恭谨慎,有时还要委曲求全,通过体制内的合理、合法、合情的正常运作,实现这他的欲求。
这也是过去,现在,将来,所有来到大城市捞世界的外省人的不二法门,尤其来自穷乡僻壤的外省青年,更是生命力特强,存活率特高的一族。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敢于投机,敢于冒险,敢于钻营,敢于巴结,甚至敢于无耻的精神,比之在优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强上百倍。由于出身清苦,处于底层的原因,这些人对于财富的冀求,权力的渴慕,往往表现得非常贪婪,有时达到病态的癖嗜。但是,他们通常不找体制的麻烦,而是在体制认可的范围里,无不达到极限地去获得一切,这种干劲,是养尊处优惯了的城市人所不具备的。
李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他具有这种外省人的心结,但不具有于连那种在体制内打拼的力气。试想,他应乡试,26岁,到河南,30岁,迁南京国子监,34岁,进北京,38岁,赴姚安任知府,50岁。这个年过半百的外省人,早过了像于连那种风华正茂的年纪。在麻城与几位小女子、小媳妇谈经讲道之余,顶多也只能流露一点柏拉图式的情愫而已。做不了,也无法做于连的他,“不如遂为异端”,挂冠而去,“宁贫贱而轻世肆志”,以逆潮流的态势,从体制外另辟蹊径,闹出一番他的天地,便是他的目标。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断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这样的评价是准确的。但是他臆断:“如果他在1587年,也就是他剃度为僧的前一年离开人世,四百年以后,很少会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姚安知府名叫李贽者其人其事。在历史上默默无闻,在自身则可以省却了多少苦恼。”他认为:“李贽的不幸,在于他活的时间太长。”其实,从这位历史人物的心理状态进行探求的话,他的最大苦恼,应该是“不甘为一世人士”,怕不出名;他的不幸,应该是担心“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仍是怕不出名。所以,他宁愿苦恼,也不愿默默无闻。
名,是他的一股无名毒火,片刻不宁地在燃烧着那颗不安的心啊!
他自杀的前两年,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年过古稀的李贽,被总理河漕的刘冬星(大概相当于水利部长的要员吧?)从南京接到济宁小住。虽然是个小城,但却是个古城,当年李白、杜甫曾经在这里作客,至今城内留有遗址。李贽看了一遭以后,感慨系之:“济上自李杜一经过,至今楼为太白楼,池为杜陵池,池不得湮,诗尚在石,吁,彼又何人,乃能使楼池之名不能灭也!吾辈可以惧矣,真是与草木同腐也哉!”
中国的士大夫,无论其为主流,抑或异端,都好名,尤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的不朽,几成一种病态。特别那些自以为是人物者,做顶天立地的大事业,为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有传之后世的大著作,立德、立功、立言,是胸臆中总在涌动的心潮。李贽属于最为严重的一位。早年,这样的抱负,多少还有点积极的进取励志之意,如今,年纪一把,行将就木,还在那里害怕自己与草木同腐,这就表明李贽到了晚年,求名的亢奋状态,非但未曾降温,甚至到了近乎谵妄的程度。
十多年前,他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给自己造灵骨塔时,就透出这种神经质。在《豫约》中嘱咐弟子:“若其真实有高兴至塔前礼拜者,此佛子也,大圣人也,急宜开门延入,以圣人待之,烹茶而烧好香,与事佛等,始为相称。”难得知己,竭诚相待,自是李贽这番话的主旨,但夸张地捧朝拜者为圣为佛,那言外之意,他这个被朝拜者,岂不是更圣更佛的上上人了吗?如此直白的自我期许,正应了清初大学者方以智对他的评论:“专骂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
李贽也不讳言:“好名何害?好名乃世间一件好事。”因此,求名、邀名、造名、醉名,陪伴了这位老爷子一生,成为他推拭不去的痛苦之源。一直到他下决心割脖子以后,才彻底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据袁小修《李温陵传》,他在气绝之前,曾与这位待诏有段对话:
侍者问曰:“和尚痛否?”
以手书其手曰:“不痛。”
又问曰:“和尚何自割?”
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最后这句话,算是他得到了真谛,至此,离上帝还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李贽放弃了一生要做在世圣人的梦。这一刀,表示了他的弃绝,他的断裂,他的转折,因为他终于悟到无须乎再追求什么了,于是可以死了。从这一刻起,升华了的他,属于他个人身影的那些部分,对于历史的他来说,逐步在减弱,在淡退,而他一生中对虚伪的儒学体系的抨击,对伪道学,伪君子,以及一切从政者的揭露,对封建社会主流意识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精神,卓尔不群思想,特立独行品质,渐渐成为历史上的他的主体或者全部,并且愈来愈光辉。
当然,也无须为贤者讳,甚至羁押于镇抚司监狱时,他在一首《书幸细览》的诗里,还幻想神宗朱翊钧读了他的《藏书》、《焚书》后,如聆纶音,立刻下了一道圣旨:着八抬大轿,由东华门进,朕要这位李老先生为国师呢!从这个极卑微,也极机会主义的细节,也看到植根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士大夫,不论其逆反主流到什么地步,悖背体制到什么程度,最后,还是服膺于皇上圣明。
他死得相当痛苦,因为他是一个爱洁成癖的人。不停地沐浴,不断地扫地,是他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消遣。平素里,凡来访贽公者,有一条规矩,都要坐得离他稍远一点,因为他简直忍受不了别人的体臭。这或许是嘲讽了,干净了一辈子的他,想不到最后以大污秽、大邋遢收场,衣衫尽染,浑身殷红,创口滴血,鬓须凝结,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狼狈场面。于是,躺在门板上的他,那本来明亮睿智的双眼,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一直熬到第二天的深夜,血流尽最后一滴,心脏停止跳动。
李卓吾活着的时候,有人恨他,有人敬他,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死了以后,仍然不能盖棺论定。有人尊他为圣人,有人憎他为败类;有人认为他是中国第一思想犯,有人认为他其实没有什么思想,不过好作大语怪论,喜唱反调的另类文人而已;有人看他为道德高尚,行为磊落的学问家,有人看他不过是周旋于权贵之门作清高状的清客;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狂热的传教士,仆仆风尘,到处宣扬他的教义,有人认为他虽然大骂“今之从政者,只是一个无耻”,但吃穿拿用,全赖这班无耻之人供给,过着优越富裕的寄生生活。他虽剃度,但不拒酒肉;他卑侮孔孟,却在佛堂里挂孔子像……如果我们将他作为一个人看待,不是先知,不是神仙,那么有高尚,也有庸俗,有伟大,也有渺小,也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但是,李贽的可贵,就像黑夜里灼目的闪电,虽匆匆一瞥,却唤醒了中国知识分子,是可以而且应该喊出一声“不”,向千古不变的封建秩序挑战。否则,口口声声“奴才该死”、“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说不定到今天我们还在黑夜里摸索。
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开始向现代社会发展,但同一时期的中国,更具国力优势。当1405年郑和率船队从泉州港启碇,向南中国海进发,欧洲还不具备如此强大的远航能力,相隔近半个世纪以后,发现美洲的哥伦布,才出生在意大利。如果,当时的中华大地上,有更多的如李贽般敢于思想的知识分子,觉得大明王朝也可能换一种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谁知道今天的中国又会发展成个什么样子呢?《明史》论朱翊钧:“明亡,实亡于神宗。”其实,中国的积弱之势,又何尝不是从明代错过了这样一个发展机遇而造成的呢!
这就是李卓吾先生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