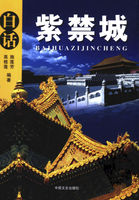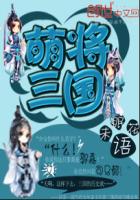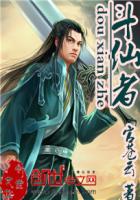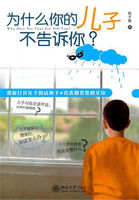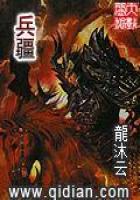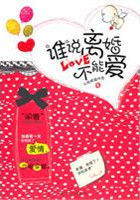有关16-18世纪以耶稣会士为主要媒介的中西关系史的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曾一度兴盛,且基本上集中在30-40年代。据相关报刊资料索引统计,这时期的刊发论文中,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之关系的论文有87篇,论传教士及其著译作品的有54篇,论传教士与中国士人之关系的有2篇;此外还有侧重于传教史的论文,其中通论传教史的22篇,论中国天主教人物的65篇。总计在不到20年间有230篇论文问世,数量不菲。1949-1979年间,港台学者在此前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向专题化发展,50-60年代刊发的论文仍有110篇左右;但是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几告停顿,仅见朱谦之、雷海宗二先生数篇论文,前后相较,颇令人抱憾。重新关注这个论题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经过数十年的断裂,近20年的研究可以说是从头开始,对30-40年代研究成果的继承性并不明显。其鲜明特点是,从译介国外资料入手,进而主要依凭外文资料进行一些专题研究(如传教士传记、欧洲汉学史、中国文化在欧洲的反响),最近几年则有不少人开始关注立足中国场景、借助中文资料来解读这段文化交流史。无论是介绍海外研究动态以与国际学术接轨,还是奠定当前的基本研究格局,或是勤于译事以提供研究资料,这20年来的新“先驱”们都可谓有披山通道之功、筚路蓝缕之业,令吾辈后学者感激不尽。与国外学术界对16-18世纪中西关系史长达百年的持续钻研相比,我们的研究毕竟仍处于新生时期,尚有许多问题等待开掘,也有许多已涉及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比如本书所要论述的中国上古史对欧洲的影响。为了说明本书的立论空间和涉笔理由,只好不为贤者讳,接下来要指出国内现有的16-18世纪中西关系史研究著作对中国上古史问题的忽略或粗疏之处。
一、国内研究状况
前几年有一些著作,从其所论述的主题而论,原该包括中国上古史问题,但事实上却显示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空白。一类是比较中国与欧洲世界观或谈论中国对欧洲世界观影响的作品,忽略了欧洲世界观的改变不仅仅是300年航海实践所带来的见闻所致,不仅仅意味着地理观念的扩大,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是世界历史观念的变化,是对欧洲和欧洲以外地区文化发展历程的重新认识,比如黄爱平《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思想文化卷》。又一类是谈论“中国观”的作品,往往偏于强调中国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孔子儒学、理学)对欧洲的影响,是欧洲人形成“中国观”的基础,此外也着重叙述以伦理道德和政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是欧洲人认识中国的重要依据,却似乎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编年史书对于塑造启蒙时代欧洲人的中国观也扮演着毫不逊色的角色,比如何兆武先生的两篇论文《清代前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和《旧制度时期的法国与中国文化》。或者即使提到欧洲人评论中国历史的言语,也是从属于那种以哲学、道德、制度为核心的“中国观”,比如朱谦之先生《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对帕斯卡《思想录》及伏尔泰《风俗论》里中国上古史观的简单介绍,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中提及的帕斯卡、维柯对中国历史的评论。
出现这种认识空白,推本溯源还在于有关此问题的中文资料匮乏,致使以往中国学者通常无从知晓中国上古史问题在欧洲的经历,自然也没有条件对它有完整体认,更不用说能在评价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各种问题时给它一个合理位置。这种空白正是本书写作的动机之一。
国人关于欧洲汉学史的先驱之作当属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1943年著),其中提到卫匡国、柏应理、马若瑟、宋君荣几位耶稣会士著有关于中国上古史的书,但点到为止,且概因资料未备,将卫匡国的《鞑靼战纪》与《中国上古史》淆为一书。
近年来随着国内西方汉学史研究和耶稣会士研究的重新兴起,论及中国文化西传的作品也逐渐增加,其中的专题性讨论(以论文为主)对科学、儒学(包括理学)、制度(如科举制)、语言、物质文化、艺术风格各有涉及,但关于中国历史知识西传的独缺。偶尔可在对中国文化西传作概述性介绍的作品或耶稣会士传记类作品中看到历史知识西传的影踪,但多数限于学术史的介绍,而且不够完整。
比较多的一类作品停留在介绍有哪些欧洲人(主要是耶稣会士)的著作传播了中国历史知识,但往往没有将中国上古编年史作为独立考察的对象。比如许明龙的论文《论意籍汉学家卫匡国的历史功绩》对卫匡国所著《中国上古史》有内容梗概,朱静的论文《巴多明神父和他的〈自然之码——孔子的诗〉》提到一句说巴多明曾将一部自伏羲至尧的中国古代史译为法文。又如许明龙的《欧洲18世纪“中国热”》一书“记述中国的著作”这部分所提到的书籍包括了谈论中国上古历史的几部书,即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志》、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李明的《中国现势新志》、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冯秉正的《中国通史》(除门多萨,其余作者皆耶稣会士),但他概述内容时并没有从这些书所记载的中国历史这个角度着眼。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介绍了晚明时期提到中国历史的西方人著作,并对内容有摘要,比如西班牙奥古斯丁会士拉达出访福建后的报告、《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在《札记》中的片羽吉光、《大中国志》、《中国新志》、《中国上古史》、《鞑靼战纪》,在文末则简要提到这些人介绍的中国历史对欧洲人很有影响。吴孟雪《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有专章谈论“欧人对中国历史的探索”,是在《明代欧洲汉学史》基础上的扩充,所提到的作品多了些,增加了柏应理的《中国帝王年表》、傅圣泽的《中国历史年表》、《中华帝国全志》,并且略微叙述欧洲思想界(如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对中国历史的反响,但这种叙述只停留在对中国文化的褒贬态度这个视角。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也简要介绍拉达、门多萨、曾德昭、安文思、卫匡国、冯秉正等人著作。
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中对安文思《中国新志》里中国上古史内容的个案研究虽然也是关于耶稣会士的知识传播研究,但与上述作品皆不相同的是,利用在华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描绘出中国编年史问题在传教士中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已经进入了思想史的讨论,比前述作品单纯的文本介绍无疑要深入得多。但他也仅止于此,对于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中国上古史在欧洲引起的问题和产生的影响没有涉及,只说由于安文思等传教士的努力,中国历史发端于伏羲的观点被西方人确认。
迄今为止,17、18世纪欧洲学者对中国上古史问题的态度这个题目,国人论及者十分少见。许明龙的《孟德斯鸠与中国》有篇幅不小的一节介绍孟德斯鸠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包括对中国上古史的看法,在以中西文化交流为主题的作品中已实属难得。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也谈到欧洲人对中国古代编年史感兴趣的原因,然而很简略,且因全书主题的关系,该问题只被引向欧洲人如何为了推断中国古史纪年而研究中国古书中的天文记录、从而开启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之门这一视角,实则仍侧重学术史的介绍。
总之,以上作品向我们传递出来华耶稣会士曾有许多人关注中国上古历史,而启蒙时代的欧洲曾从这些信息中受益,比起前人来填补了很大的学术空白。但是,它们无一完整地叙述中国上古史问题在中国传教士和欧洲学者中间发生、发展的过程,也没有把相关的传教士作品和欧洲学者作品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分析,这也是促使撰写本书的又一个原因所在。
而有一些力图全面勾勒中国文化西传状况的论文竟全然没有把中国历史知识纳入视野,不能不说是重大缺陷。比如黄启臣的综述性文章《16-18世纪中国文化对欧洲国家的传播和影响》谈到儒家哲学、重农思想、四书五经、语言文字、古典文学、中国医学、工艺美术、绘画建筑、中国风俗这么多内容的西传,可是只字未提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
目前可见的谈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表现出一个明显倾向,喜欢把18世纪上半叶欧洲尤其是法国的“中国热”作为一个核心事件描述,上面提到的多数作品不约而同有这种偏好,此外又如王宁、钱林森、马树德《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等几部专著,以及严建强的论文《“中国热”的法国特征及其解释》。我并不是反对强调标志性事件的意义,也不是否认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在18世纪中期达到顶峰,只是认为在渲染标志性事件的同时也该同等程度地关注标志性事件前前后后的漫长时期。“热”与“非热”本是人为划分的相对性区别,本质上它们都是一个长期过程的连续组成部分。不能把标志性事件孤立地突出,不能在研究文化交流时眼光只放在高潮、热点,却忽视了文化传播与文化影响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在考虑文化的思想层面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换而言之,我们还需要了解作为一个持续发展过程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面目。中国上古史问题与“礼仪之争”、“中国趣味”有所不同的一点是,有关它的讨论在100多年里保持着相对平稳、和缓的发展态势,尽管期间也曾有过集中和够称激烈的争论,所以它是体现启蒙时代欧洲人之中国观的渐变性特征、乃至欧洲人思想中渐变性特征的上好课题。
二、国外研究状况
国外早期关于中西文化交往的通论性作品中存在一个类似中国学术界的问题,重视18世纪欧洲在艺术风格和生活趣味上的“中国热”,重视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哲学、制度和道德文化的青睐,对于中国上古史在欧洲思想进程中的表现却不着一字,比如大名鼎鼎的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1923年初版)与赫德逊《欧洲与中国》(1931年初版)。这两部著作的欠缺所反映出的问题不仅仅是20世纪前期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全面,而且还是当时的西方学者对“启蒙时代”这样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话题的认识有失单调片面,背后所隐藏的是整个史学思维的时代特征——偏爱激动人心的变革,偏爱变革时代里尤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通论中西文化交流的作品中就出现了以西方的“中国观”或“中国形象”视角组织材料的一类,20世纪后半叶这一视角更为流行。然而这类作品在论述启蒙时代欧洲人的中国观时,对中国历史的观念仍奇怪地常处于被忽略的地位,所重视的依然是欧洲人的中国哲学观、中国道德观、中国制度观。若提及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则已是19世纪的欧洲,此时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国历史古老悠久而没什么变化,欧洲人表述这类观点时持有一种与己无关的旁观者心态,似乎中国历史不曾与欧洲人的思想发生过联系。这样的著作较早的如M·G·马森《西方的中华帝国观》(1939年初版),R·道森《中国变色龙》(1967年初版),比较晚近的则有马凯瑞斯《西方的中国形象》(Colin Mackerras,Western Images of China,1989年初版)。
与前述作品有别,雅克·布罗斯《发现中国》(1981年初版)也是以中国形象的演变为线索,但他关于启蒙时代的内容比较偏重分析中国形象在特定的欧洲思想背景下形成的原因,而不是单纯介绍“形象”,由于把欧洲思想进程作为背景引入,在他的叙述中出现了“中国上古史问题”,惟其太过概要简略,这主要是受制于全书的通论性、概括性特征。就这种写作思路而言,《发现中国》更接近下文要介绍的毕诺和安田朴的著作。法国华裔学者丁兆庆写于20世纪初期的著作《1650-1750年间法国人对中国的描述》(Ting,Tchao-ts'ing。Les deions de la Chine par les fran?ais,1650-1750.Paris,1928.)是对这一时期法国各界人物论中国言论的辑录,但其意旨似乎也是为了通过对这些材料进行一定的编排而呈现出法国人的某种“中国观”,其中有一章是“法国人论中国的历史”,罗列了当时法国人撰写、翻译的大量中国史著作,只可惜无缘以见。
在汉学史或传教史的研究中也可以见到关于中国上古历史的内容。比如在“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的起源”这样的主题下介绍某位耶稣会士及其谈论中国历史的作品,典型的有孟德卫(D。E。Mungello)、劳端纳(Doanld F。Lach)及范克雷(Edwin J。van Kley)对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的介绍,伦德拜克(Knud Lundbaek)谈论马若瑟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又如在耶稣会士的传记类作品中涉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或传播,如柯兰妮(Claudia von Collani)关于卫匡国《中国上古史》的论文,孟德卫对柏应理《中国帝王年表》的介绍,魏若望(John W。Witek)讨论傅圣泽的中国上古史观。还有关于欧洲汉学先驱的专论,如法国汉学家叶利世夫(Danielle Elisseeff-Poisle)夫人的博士论文《尼古拉·弗莱雷,18世纪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中国观》(Nicolas Fréret(1688-1794)。Réflexions d'un humaniste du XVIIIe siècle sur la Chine。Mémoires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no。11.Paris,1978),谈论的主人公弗莱雷正是18世纪欧洲学者里对中国古代史最有研究的一位,文章讲述了他如何获取有关中国的材料,如何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真实性作出研究和判断,如何试图用中国知识来解决他有关历史和哲学的一系列问题。此文亦同丁兆庆之书闻名不能见面,亦令本论文失去可能很重要的依凭。这些研究主要针对某个人或某部作品,就耶稣会士和欧洲学者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这个问题来看,可能尚缺乏通贯性的论述。
从欧洲思想史角度讨论中国上古史问题在西方学者中占相当分量,这类作品注重分析中国上古史问题如何同启蒙时代欧洲思想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质疑和反对《圣经》权威——相契合,从而成为欧洲思想变迁中的一个积极推动因素。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法国哲学思想史专家维吉尔·毕诺(Virgile Pinot)《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1932年初版),书中对此问题在1740年之前的提出、发展、对基督教世界的震荡有透辟分析,并提供了不少当时论及此问题的作者与作品名录。法国著名汉学家安田朴(René Etiemble)《中国之欧洲》第二卷(1989年初版)亦有两章专论该问题,对中国上古史问题在1740年以前的历程介绍较略,但对1740年以后伏尔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及其相关言论论列颇多,恰可视为毕诺作品的续补。不仅如此,两人看待此问题的角度、思想倾向、叙述思路乃至叙事风格都可以说同声相应,尽管两部作品问世年代相隔久远,两位作者的研究领域也有很大差别。也就是说,他们都侧重于描绘出一个围绕中国编年史问题的针锋相对、硝烟弥漫的战场,突出中国编年史对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发展有“革命性”作用,而且他们对18世纪中期以前尚比较保守的思想环境、不属于激进派的人物和言论持有一种伏尔泰式的冷嘲热讽,对中国却抱有明显的同情和偏好。作为初学者阅读毕诺和安田朴的作品,会感到兴趣昂然,甚至可以说“过瘾”。我正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才得知中国学者鲜有提及的这个问题原来曾在欧洲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原来中国上古史问题的重大意义不在于它是欧洲汉学史的母题之一,由此而产生了进一步追究此问题的意愿,并意识到应该沿着“欧洲思想史”这个方向行进。
但是,当作为一名研究者来审视这两部作品时,又发现它们鲜明的论战色彩和强烈的思想倾向虽然是它们引人注目的特点,却也成为它们的局限性所在,会妨碍对事实的全面认识。例如毕诺,他虽然引用了许多17世纪和18世纪初谈论中国上古史问题的作品,但是他对这些材料的取舍服从于他制造论战场景的需要;如果要追问这些人的作品到底写了些什么,到底如何谈论中国上古史,就会发现毕诺介绍不多,留给读者脑子里的除了毕诺所强调的一个观点——大家越来越倾向于怀疑世界性洪水而相信中国历史的古老性、中国上古史对教会权威有巨大破坏性——之外,常常就是空白。由于注意到这一点,就开始避免对毕诺、安田朴或其他论战类作品论述基调的迷信,而更加注重这些作品包含的事实信息,力求通过汇总事实信息来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鉴于此,范克雷的作品就有了更大参考价值。
范克雷的论文《欧洲之“发现”中国与世界史的书写》(‘Europe's‘Discovery'of China and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是关于中国上古史问题文献学研究的经典之作,坚持他与劳端纳合著《在欧洲形成之时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时的文献学思路,罗列了17世纪中到18世纪末涉及中国上古史的欧洲人作品50部左右,并有详略不等的内容介绍。但范克雷的文章不仅仅是通过文献介绍展示出中国上古史问题波及面之广和影响时间之长,他还蕴涵着一种思路,即以“中国上古史问题如何影响着启蒙时代欧洲人的世界史视野”来贯穿这些文献,所以也可以属于思想史的角度。其实正是因为他在组织文献时持有特定的思想,他并没有穷尽当时欧洲所有论及中国上古史的文献,仍然是有选择的。至于这个文献规模到底有多大,因作论文的时间与空间限制,我当然无力回答,但肯定大到让任何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人都无法忽视这个问题,正文中综合所能得到的各种信息制作了一张文献表,列举出150多部(篇)。
回到范克雷的文章上来,他所提供的视角仍然属于欧洲思想史范畴,但与毕诺、安田朴和雅克·布罗斯有不同侧重,如果说后者强调中国上古史对欧洲传统思想的破坏性作用——打击教会和《圣经》关于人类和真理起源的说教,范克雷则试图说明中国上古史对欧洲思想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建树性作用——帮助欧洲人重新认识世界和人类历史。而且毕诺等人想表现的是思想史进程中一种比较激烈的变化,范克雷则传递出一种缓慢渗透式的变化。把这两类思路糅合起来,就能够对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变迁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可以说我主要是受这两种叙事启发,试图在欧洲思想变迁的框架之下对中国上古史事件进行一个全景描绘,并期望由该事件来透视整个启蒙时代欧洲思想界的主要特征。当然,限于资料不可能绘制出真正的全息图,只能力求将它所涉及的领域和影响到的层面都展现出来。
西方学者对明清中西文化关系和中国上古史问题虽然有许多研究,但他们的研究中有一个普遍缺陷。西方学者研究明清时期欧洲人的中国观,或者对欧洲有重要影响的耶稣会士著作时,经常有一处不足,就是对于耶稣会士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无法进行追根究底的分析。这个形象是欧洲人认识中国、讨论中国的基础,它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特点是什么,这都应该是评价欧洲人之中国观的前提。关于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塑造特定中国形象的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耶稣会士的宗教立场和传教中的策略需要,这是决定塑造什么样的中国形象的根本性原因,也是西方学者普遍重视的一层。另外则是耶稣会士刻画中国形象所依据的中国文献材料,这是耶稣会士中国观形成的重要因素,进而又影响到欧洲学者对中国的想象和评价。但西方学者对此着力不多,往往只能直接采纳耶稣会士的公开或私人文献中提到的材料来源,而耶稣会士出于多种原因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语焉不详,或者给出错误声明,以致今天对于一些论名字耳熟能详的耶稣会士作品如《中国上古史》和《中华帝国全志》,若追究它们究竟依凭哪些中国文献编译而成,却无人能答。就目前所见,在分析耶稣会士作品的中文依据时做得较好的是丹麦汉学家伦德拜克对马若瑟的研究和魏若望神父对傅圣泽的研究,然而这在绝大程度上归因于马若瑟和傅圣泽在自己的作品中说明参考了什么文献,而且有些还附有中文名称。但像卫匡国、安文思、柏应理等更多不明示自己资料来源的人,西方学者多半束手无策。
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由于语言限制而难以深入,这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他们研究耶稣会士时的思路。当代西方学界关于17-18世纪耶稣会士研究的一个新趋势是日渐把眼光从西方转向中国,关注这一时期有关天主教的中文原始资料,认为“这些资料甚至更直接地与汉学相关”,而且目标指向研究耶稣会士置身其中的中国社会环境,研究文人学士接受西学同中国17世纪思想运动的关系,研究中国人对西学的回应模式。把这些新的研究目标同发展得更成熟的研究传统——论述欧洲传统因素与“适应策略”的一致性和密切相关性——相比,我们发现西方学者无论立足欧洲还是立足中国,无论是埋首于西文原始材料还是中文原始材料,无论是从传教史的角度还是从汉学史的角度或是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无论是采用叙事法、阐释法,还是对历史事件、时间和资料进行考证汇编,耶稣会士中国观的具体中国来源都没有被当作一个专门性问题提出。它在这么多视角和议题中并非真的被彻底忽视,而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所看到的是有些西方学者想搞清耶稣会士著作的中国文献依据,但却显得力不从心而只能浮光掠影,这种尴尬可能是他们无法将此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出的原因吧。
中国学者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理应更有作为,可惜的是国内从事西方汉学史研究的学者多简单因仍耶稣会士或西方学者之论,任凭模糊或错误之处流传,比如吴孟雪《明清时期》一书中称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曾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纲目前编》译为法文并在北京出版,可是司马光根本没有写过名为《资治通鉴纲目前编》的作品。至于有人提到说巴多明“曾以法文翻译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部分内容”,恐怕更是以讹传讹。巴多明译文的蓝本究竟为何,在正文中会有辨析。又比如孟德卫在《神奇的土地》(Curious Land)一书中将《中国上古史》所列的帝王年表与1938年上海版《辞海》所附年表对比后发现两者差异甚小,明显的差异只是卫匡国自伏羲开始,《辞海》则从黄帝开始;卫匡国在帝喾之后紧接尧,《辞海》则在两者间插入帝挚;禹之前诸帝(包括禹)的登基时间有1-3年的差异。孟德卫由此得出结论,“卫匡国的编年史差不多是现代中国编年史的准确复制品”。这样的结论其实没什么价值,因为我们需要了解的不是卫匡国与现代中国编年史间的异同,我们希望知道的是卫匡国在写书的当时依据了什么文献,卫匡国是否提供了“准确复制品”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判断;而且把卫匡国的年表同1938年的中国年表进行比较并不正确,至少应该先搞清楚1938年版《辞海》的年表来自何方,再判断两者是否适合比较。尤其是,卫匡国与1938年版年表的细微差异被孟德卫揭示出来,却被他作为判定两者相符的依据,然而这实际上恰恰是说明两者有不同来源的证据。在中国各种文献中,自周代开始的朝代编年基本一致,而关于周代以前的编年则多有差异,这些差异构成各文献的特点之一,卫匡国与《辞海》年表的差异看似细微,却可以见微知著,实乃探究其来源的重要线索之一。孟德卫不了解中国文献,以为差异甚小就可视为误差,这是西方学者的局限,无法苛求他们去顺藤摸瓜探明真相。然而许明龙在《欧洲18世纪“中国热”》中不加考虑地引用了孟德卫这条说明不了问题的“结论”,这就属于中国学者的失察。早年阎宗临先生的博士论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中关于《中华帝国全志》的部分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可见的对此重要著作的专门研究,但是由于此论文在法国完成,完全基于西方文献,故也存在类似问题,只揭示出此书在汇编耶稣会士材料中的忠实度问题,没能揭示出它的中文文献渊源,颇引以为憾。
还原当年耶稣会士作品所依据的中文文献是个艰难的任务,也很可能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西方学者做这件事会受中文能力制约,中国学者涉足其间却又常常要为耶稣会士作品写以各种欧洲语言而犯难,如果作为一项长期和系统的任务开展,非常有必要由中西学者携手进行。本书意欲在这方面做些尝试,这也是论文思路所要求而不得已为之,因为如能知道耶稣会士介绍中国古代历史所依据的文献,就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的思想倾向怎样左右着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具体内容的取舍,而他们又把这种理解传递给欧洲人,欧洲人则根据自己的时代需要来判断和利用有关中国的这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