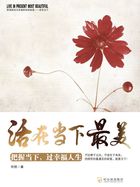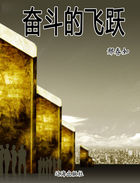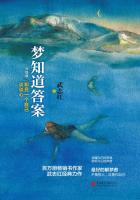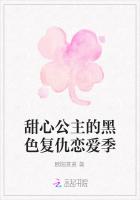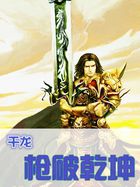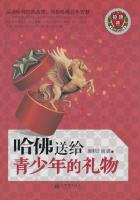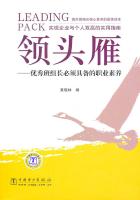现实社会中,没有人不会在某些时候遭到人们的误解甚至反对的,但是,我们不必过于认真,非得要计较和争辩。时间久了,事情也就有了变化。
你听过塞蒙·纽康这名字吗?这个人出生于1835年,卒于1909年。在莱特兄弟首次飞行成功前一年半,他说了以下的“名言”:“想叫比空气重的机器飞上天,不但不可能,而且毫不实用。”
你知道约翰·莱特福特吗?他不但是个博士,而且当过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这部名著前夕,他郑重指出:“天与地,在公元前4000年10月23日上午9点诞生。”
狄奥尼西斯!拉多纳博士生于1793年,曾任伦敦大学天文学教授。他的高见是:“在铁轨上高速旅行根本不可能,乘客将不能呼吸,甚至将窒息而死。”
1786年,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初演,落幕后,拿波里国王费迪南德四世,坦率地发表了感想:“莫扎特,你这个作品太吵了,音符用得太多了。”
国王不懂音乐,我们可以不苛责,但是美国波士顿的音乐评论家菲力普。海尔,于1873年表示:“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要是不设法删减,早晚会被淘汰。”
乐评家也不懂音乐,但是音乐家自己就懂音乐吗?柴可夫斯基在他1886年10月9日的日记上说:“我演奏了勃拉姆斯的作品,这家伙毫无天分,眼看这样平凡的自大狂被人尊为天才,真教我忍无可忍。”
有趣的是,乐评家亚历山大.鲁布,1881年就事先替勃拉姆斯报了仇。他在杂志上撰文表示:“柴可夫斯基一定和贝多芬一样聋了,他运气真好,可以不必听自己的作品。”
1962年,还未成名的披头士合唱团,向英国威克唱片公司毛遂自荐,但是被拒绝。公司负责人的看法是:“我不喜欢这群人的音乐,吉他合奏已经太落伍了。”
你听说过艾伦斯特·马哈吗?他曾任维也纳大学物理学教授,生于1838年,卒于1916年。他说:“我不承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如我不承认原子存在。”
爱因斯坦对以上批评并不在意,因为早在他10岁于慕尼黑念小学的时候,任课老师就对他说:“你以后不会有出息。”
严格说来,遭人反对、小看不是坏事,这可以提醒我们争取进步。可是,人身攻击就令人难以忍受了。
法国小说家莫泊桑,曾受人批评为:“这个作家的愚蠢,在他眼睛上表露无遗。那双眼珠,有一半陷入上眼皮,如牛看天,又像狗在小便。他注视你时,你会为了那愚蠢与无知,打他100万记耳光仍觉吃亏。”
就算西方文学的大宗师莎士比亚也有阴沟翻船的时候。以日记文学闻名的法国作家雷纳尔,1896年在日记中说:“第一,我未必了解莎士比亚;第二,我未必喜欢莎士比亚;第三,莎士比亚总是令我厌烦。”1906年,他又在日记中说:“只有讨厌完美的老人,才会喜欢莎士比亚。”
这位雷纳尔先生爱说俏皮话,他在1906年于日记中说:“你问我对尼采有何看法?我认为他的名字里赘字太多。”连名字都有毛病,文章如何自不待言。
英国作家王尔德,也以似通不通的修辞技巧,批评萧伯纳说:“他没有敌人,但是他的朋友都深深地恨他。”
思想家卢梭54岁那年,即]766年,被人讽刺为:“卢梭有一点像哲学家,正如猴子有点像人类。”
戴维·克罗克特有一句很简单的座右铭:“确定你是对的,然后勇往直前。”
每一个人,不论是贩夫走卒还是英雄人物,总有遭人批评的时刻。事实上,越成功的人,受到的批评就越多。只有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才能免除别人的批评。真正的勇气就是秉持自己的信念,不管别人怎么说。
许多人觉得自己生活不开心,因为他们太过于注重别人的看法,这样的人,无异于是在“为别人活着”,一举一动都受别人的评论所左右,结果限制了自身能力的充分表达。
有的人对别人没有讲出口的话或对别人无意的批评和非议过于敏感。假若你觉得受人藐视(不管是真的或想象的)而心有所感,那么别为此而跟人斗气。指责别人对你有恶感或对你冷淡,可能会让你一无所得,而且容易引起摩擦。反而惹出你心理上早就预料到的反应。要承认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每个人都可能犯片面的错误。
密切注意自己对别人的态度:你是否太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力求尽善尽美的同时,是否隐藏着内心的消沉?对别人的批评你是否耿耿于怀?假若确实如此,那么你该自省,并订出更符合于自身利益与技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