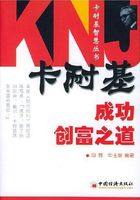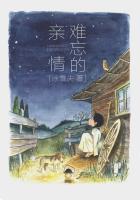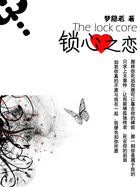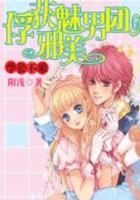圆,是为了减少阻力,是方法;方,是立世之本,是实质。外圆内方,并非老于世故、老谋深算的“狡猾者”的处世哲学,每个人都可以借鉴其中的积极思想。
船头,为什么不是方形而总是尖形或圆形的呢?是为了劈波斩浪,更快地驶向彼岸。人生也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较量,拼个你死我活,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争取最后的胜利?生活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事事计较、处处摩擦者,哪怕壮志凌云,即使聪明绝顶,也往往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结果。为了绚丽的人生,需要许多痛苦的妥协。
旧中国,在封建高压下,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许多正直而又有智慧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1935年,蔡尚思写就《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前辈欧阳予倩曾谆谆告诫这位青年史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以“纯研究的态度”作进攻的“挡箭牌”,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予倩感叹谓:“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润,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
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之一黄炎培即是典型。“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他亲笔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第三方面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当蒋以“教育部长”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沼时,黄却不为所动,答以“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
外圆内方是一微妙的、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保全了人才的精华,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使人格主体为把握正义和生存的平衡艰难地度量着。
1947年底,在国民党的淫威下,黄炎培代表民盟被迫与当局达成自动解散民盟的协议。尽管此举避免了广大盟员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但黄炎培良心上的失落感却使他极其痛苦不安,吟出“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的诗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人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
为人处世要方圆兼顾。只圆不方,是一个八面玲珑、滚来滚去的“球”,很难在社会上立稳脚跟。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一个成熟的人,不论处在人们可以想象还是无法想象的困境,他都矢志不移、义无反顾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以求对人类、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这,便是所谓的“方”。把“方”和“圆”完美地结合起来,才能左右逢源,无往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