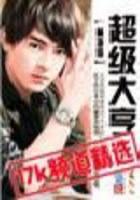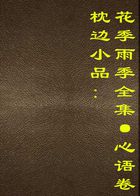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了父亲的头上,父亲已被松陵村的革命群众斗争了三场,公社党委决定,要给父亲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材料已经上报到县委去了。父亲的主要罪行是搞破坏。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对父亲来说。
那天早晨,生产队长派父亲去犁莽麦地。莽麦收获没有多少时日,葬麦地本来就不太僵硬,加之刚下了一场雨,莽麦地就很酥软了。
犁伴犁过去,犁耳子上沾着厚厚的泥条,一张铁犁足足有四五十斤重。每到地头,父亲回犁就有些吃力,他一面用脚使劲地蹬缠在犁铮上的泥土,一面用“出绳”(拴在牛鼻圈上柬缚牛的皮绳)使劲地拉牛。牛的舌头从牛笼嘴(一种用竹箴子编的农具,戴在牛嘴上以防牛耕地时吃草)里伸出来在地上揽。莽麦地两边都是深沟,野草长在沟边,牛费了很大劲也揽不上一口。两头牛不管揽草危险不危险,哪怕吃上一口摔到沟里去栽死,牛也不管不顾。一个早晨,父亲提心吊胆,生怕牛滑到沟里去。父亲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小心翼翼地犁着地,总算没出什么事儿。可是,就在他准备收工,犁最后一个来回时,两头牛一到沟边看见野草就拼命地揽。两头牛做出的是一副宁愿为一口吃食跌死也不愿为一口吃食想死的姿态。父亲放下犁把,一双手抓住“出绳”使劲地向回拉牛,牛使劲地和父亲对抗。父亲怎么拉,也拉不回来牛,牛的头弯下去,只顾揽草,眼看前腿向沟下边一点一点滑去了,它们全然不觉。父亲套犁的“出绳”是断成两截后续接到一块儿的,续接的地方松动了。如果牛是乖觉的,如果父亲不使劲拉“出绳”,松动的地方不会出麻达的。父亲拉了一个早晨,“出绳”终于从续接的地方松脱了。
“出绳”一断头,两头牛没了束缚,便像箭一样向沟底里射去了,连带着铁犁。父亲大概出于本能,松开了抓住“出绳”的手,他一闪,跌坐在沟边了。父亲立时六神无主,脸色蜡黄,呆呆地坐在沟边,一眼也没有看跌下去的两头牛。冰凉的太阳光从他的身上淋下来,秋风将父亲的衣襟卷起来了,他如同一摊烂泥。
饲养员老汉等着喂牲口,他等不住了,撵到地里来找牛,父亲才如梦初醒,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天早晨,只有父亲一个人在莽麦地里犁地,无论他给谁说,谁也不会相信牛是挣断了“出绳”跌到沟里去的。就是有人目击到了事情的过程,也未必能替父亲作证。一头牛跌下去当即就死了,一头牛虽然没有死却跌断了腰,站不起来了,只能卖到肉坊里去,不能再耕地了。父亲在被斗争的时候很可能后悔当初在惊恐中没有一同和牛扑下去。我猜测,父亲也曾冒上来这么一个念头,可是,他一看那黑洞一般、张着吃人的大口似的深沟,不由得害怕。
也许,父亲于一刹那间意识到了,一旦他扑下去,命运和被吃了牛肉的牛是一样的。假如父亲抓住“出绳”的手不松,让两头牛把他也带到深沟中去,他的痛苦在这天早晨就被解除了。
在斗争会上,生产队长的发言一根棍子似的猛然间将父亲打醒了。“狗地主,你的命有一头牛重吗?牛跌死了,还能吃肉,牛皮还能合成皮绳,你死了,狗都不吃。”父亲怎么没有想到,他的命没有一头牛重?他大概觉得,他是人,就是地主也是人。
上台发言的革命群众将蓄意破坏的罪名硬是按在了父亲头上。
会场上响彻着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倒地主反革命分子!”“老实交待!”
松陵村的一个初中毕业回来参加了生产劳动的小青年上台去念了一首顺口溜“远望南山光有光,一斗谷子十升楝,鞍子匹在石头上,独木桥上下凌霜。”小年轻人说这是父亲当大队会计期间写的,是诬蔑社会主义、诬蔑共产党的反动诗歌。革命群众问父亲是不是他写的?
父亲说是。不要说让父亲承认他写了反诗,就是叫父亲承认他杀了人放了火,父亲也会毫不迟疑地画押的。父亲已经无所谓了,有没有罪状是一样的,有几十条罪状和有一条罪状是一样的,承认不承认也是一样的。父亲只是盼望着斗争会尽快结束。他的脖子上戴着几十斤重的木板,他受不了那皮肉之苦。难怪,有一个革命群众说:“狗庸的也是你罗世俊屑的,你说是不是?”父亲连声说:“是,是。”
那天下午,父亲被松陵村的革命群众牵着去其他大队游街。父亲的脖子上挂着大木牌,脊背背着一张剥下来的牛皮。牛皮散发的比牛皮更厚实的腥臭味儿被他带到了全公社的每一个生产大队。父亲的面部污脏,头发长了没剃,胡子也长了,他苍老了许多。
走到朱家庄,父亲的腰弯得更厉害了,披着牛皮的他看起来不是牛也不是人,好像一个怪物。父亲已不能面对外祖父家的每一个人了。父亲像小学生背课本似的将自己的罪行向革命群众交待了一遍。
父亲抬起头来时,眼角里的余光扫见了母亲。母亲站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她的表情平静而麻木。母亲似乎目击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舞台上的一个丑角;母亲似乎只是在观看一出秦腔戏,对剧中的人物不同情怜悯,也不憎恶讨庆,她不过是一个观众而已,一个不参与剧情,只图热闹的观众。父亲看见,母亲的身后站着一个男人,这男人像高粱轩一样细,有一双尖锐的老鼠眼。那男人正和母亲谈什么,母亲回过头去看看那男人,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父亲的头使劲向上一仰,扫了母亲和那男人一眼,那男人将细瘦而少肉的右手放在了母亲的肩头,脸上的笑也是细瘦而少肉的。父亲突然大叫两声,随之,扑倒在地,人事不省了。
父亲病了。
父亲在炕上躺了两天。祖母给父亲请来了村里的胡大夫。胡大夫给父亲诊了脉,察看了父亲的舌苔和面部的颜色,捋着花白胡子对父亲说:“娃呀,我知道,心病要作心药治。我劝你几句,也不一定能起啥作用的,我就不费口舌了。我给你开三服药,你吃吃再看吧。”老头子戴上了老花镜,从一个小布包里取出来一方黄铜砚盒子,铺开了一方淡黄的纸,给父亲开了一个药方。
祖母拿上药方,去公社卫生院抓药。三服药总共是1块4角6分。祖母身上只有1块3角钱。她求抓药的年轻人给她欠个账,抓药的说:“不能欠账,一分钱也不能欠的。”祖母再三思求,抓药的还是不开口。祖母就去找院长,院长也是个中医,差不多有60岁了,善眉善眼的,一副富态相。他进了中药房。将抓好的三服药解开,把药中的白术和夜苓分别向出取了两片,然后,包好药包,给了祖母。祖母便对这院长千谢万谢。
回到松陵村,祖母将药煎好之后端给了父亲。父亲不喝药。祖母无法再劝慰父亲了,她知道,父亲的心里比中药还苦。祖母嗅到的不只是中药的苦味儿,她嗅到了来自父亲身上的那种似乎不掩饰的气味,不再为活着而煎熬的气味,那气味是从父亲木然的眼神里,是从父亲绝望的脸庞上,是从父亲躺在炕上的毫无款式的姿势上散发出来的。这气味使祖母心痛不已。祖母不愿意将她已窥视出来的来自父亲心底的秘密挑破,她很难面对她的预感,那将使她心痛欲裂!祖母对父亲还抱着希望,她用自己对父亲的爱来感动父亲,然而,父亲已无动于衷了。
药碗里的中药渐渐地凉了,那苦味儿也干瘪了。祖母叹息了一声,“世俊,起来喝吧,不要作践自己了。”
父亲的日光紧紧地盯着房子门后面。事情发生以后,祖母才知道,父亲盯住的是挂在房子门背后的那根麻绳。父亲将目光收回来,看了看祖母,他欠起了身子,坐在炕沿,端起药碗一口气喝光了药。
连吃了三服药以后,父亲下了炕。
父亲坐在院子里,将麻绳断了以后续接的穗头重新续了一遍。祖母一看父亲在一丝不苟地续绳,就说:“你躺着去。你不用它,忙着收拾干啥呀?”这麻绳是夏收时用来绑架子车上的麦捆用的。父亲没有回答祖母,他只是苦笑一下,继续干他的活儿。
父亲拄着一根木棍在田野上走动着,从坡上到坡下,从东边到西边,不慌不忙,不紧不慢,他大概知道自己最终要走到哪里去,该走多少路程,需要多少时间。对村子后面的北山,对田地里已显出了绿色的嫩嫩的麦苗儿,对路旁的树木和尚未干枯的野草、野花,父亲都抱着极大的兴趣。他看一会儿,闭上眼睛站一会儿,似乎要让他目击到的所有事物像装粮食似的全装进一个口袋,一粒也不剩。父亲像一个土地丈量员,用脚步丈量了田地,又去丈量村庄。走到材口的那棵大松树下,父亲抬头凝视,这是一棵永不衰老的树。父亲做孩子时,松树是这样子,几十年后,松树还是这样子,威严、冷峻。树上的针叶未曾变淡变浅,树下的阴影未曾变淡变稀。这棵古老的树使父亲胆寒。父亲是在松陵村的这块土地上长大成人的,父亲是在这棵松树下生活着的,至今,他对这块土地这棵松树也没有弄懂。
父亲从地里回来了。他从抽屉里翻出来两枚铁钉,抢起斧头,向那个柴木凳子上钉铁钉。一枚铁钉被他钉歪了,他用手钳拔出来,又钉第二枚。斧头的盖子总打不到铁钉子上去。柴木很硬,父亲钉不进去。刚刚从电磨子上磨面回来的祖母一看,父亲在钉子上乱砸,就说:
“凳子好好的你给它钉钉子干啥呀?”父亲说:“它不稳当了。”祖母放下面袋,抓起凳子向地上一放“咋不稳?你试试,稳稳当当的。”父亲撂下斧头,他用手在眼窝上揉了揉。凳子大概在他的目光里摇摇晃晃着,他看不清了。
当父亲能够从从容容地行走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他大概觉得,已记住了这块土地上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一切景象了,这块土地使他得到了暂时的平静。但是,当他真正地意识到他将不再牵挂这块土地的时候,他不愿意在田地里走动了。他躺在炕上不下来,发冷似的在被窝里抖动。盖着一条被子不行,又加盖一条被子,不一会儿,他大汗淋漓了。他蹬掉了被子,坐在炕上,呆呆地看着窗外。
父亲睁开眼睛躺着,他不愿意合上眼皮。一闭上眼睛,他大概看见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大概觉得,身处在黑暗中,无异于处在“无”的状态下,黑暗代替了全部感觉,他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了,他的血肉、神经、灵魂不再参与人世间的一切了,他的知觉暂时停顿了。他只是睁大眼睛大口大口地喘气,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轻松一点。
哥哥从学校里回来吃午饭。饭碗端在手中还没有下口,父亲在房间里大虎大虎地喊他,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父亲喊得很急迫,他就端着饭碗进了房间。他一看,父亲的饭碗依旧放在炕边,好像一口也没有吃,碗里冒着热气。父亲蹲在炕上,看了看哥哥:
“想不想你娘?”
“不想。”
“不想?”
哥哥急于吃毕午饭去学校,他端着饭碗正要离开房间,父亲叫住了他:
“大虎,你说,你为啥不想你娘?”
“不想就是不想。”
我的哥哥罗大虎没有料到,父亲突然端起饭碗向他摔过来了。儿子不想母亲,是做父亲的难以容忍的事情。我看得出,在父亲的眼里,儿子的母亲就是有错误,做儿子的也要原谅她,绝不能抱怨母亲,更不能给母亲记仇,这是父亲对儿子最起码的要求!不知是父亲力气不够,还是他压根儿不想将饭碗摔在儿子的身上,饭碗摔在了脚地,碗碎了。哥哥一下子被吓住了,父亲从来没有这样过呀。他一看父亲扑倒在炕上了,流着眼泪一声一声叫爹。父亲摆摆手,叫他走开。这时候,祖母闻声进来了,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责备父亲:“世俊啊,你有病,还发啥脾气呢?得是大虎惹你生气了?”父亲抬起埋在被子里的头,擦了一把泪水后说:“不怪大虎,怪我自己。”
祖母给哥哥摆摆手,叫哥哥快去学校。哥哥走到炕跟前,扑通一声跪倒了,他哭着说:“爹,怪我,全怪我。”父亲拉住了儿子的手,用泪眼看看哥哥,一句话也不说。祖母将我的哥哥罗大虎扶起来,叫他快去学校,清扫了脚地的汤饭,她重新给父亲自了一碗饭。这一顿,父亲没有吃,他大概又在思念母亲了。
父亲整天流眼泪。祖母不在的时候,他就放声哭。祖母如果在家里,他就拄上棍子去田地里哭。他边走边哭,边哭边走。泪水顺着瘦削的面颊往下流着,那几乎干洒了的眼睛由于泪水的湿润而变得模糊不清。他走了几天,还是走不出松陵村。这个村子像绳索一样把他捆住了,他走了30多年也没有走出去。
那是一个冰冰凉凉的夜晚。月亮躲在薄云里面,透出来的月光朦朦胧胧的,大地似乎撩不开面目,人所能目击的事物都是影影绰绰的一团。天一黑,父亲穿戴整齐要出门去。祖母就问他要去哪搭?父亲说他要去朱家庄。祖母说:“你身体不好,不要跑冤枉路了,仙娥会回来的,时间还没有到哩。”祖母的这一句话不知触动了父亲的哪一根神经,他突然站住了。他大概在揣摸祖母所说的时间是什么?他大概在想,人活在世上还不是和时间较量吗?父亲知道,人是永远也较量不过时间的。“啥时候就到时间了?”父亲仿佛是自言自语。祖母说:“她在娘家住不下去的那一天就到时间了。”父亲苦笑一声。“时间到了,我看时间到了。”父亲出了院门。祖母没再拦他。
父亲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多回了。脚下那条灰白色的路面像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向前拽,他似乎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路两旁的树木和田地看不见头顶阴沉沉的天和从云层里钻出来的那几颗微弱的星星。朱家庄就在眼前头。父亲扶住了一棵树,他抬起来了头,张开眼,他看见的肯定只是一团混沌不清,是连轮廓也长了毛似的模糊状态,父亲顺着一棵小树溜下来坐在了路上。他将头埋在两膝间,一动也不动,除了冷风在树的枝叶间窜动所发出的轻微的声响以外,四周没有任何声音,大地仿佛被装在袋子里封存了。在几声凄凉的狗叫声中,父亲站起来了。他抓住树身,叫了一声仙娥,眼泪长淌。父亲扔掉了手中的木棍,他磕磕绊绊地向前走,不是碰在路旁的树木上,而是碰在了看不见摸不着的夜色上,碰在了看不见摸不着的时间上,父亲的心被碰痛了,身体被碰得弯成了一张弓。父亲就这样摇摇晃晃着向朱家庄走去了。
到了外祖父家的院门前,父亲看了看那扇厚重的大门,手举起来,抓住了门环,他在圆圆的生了锈的门环上摸了摸,还没有动手拍,手一松,身子顺着门溜下去了。父亲趴在院门前,一遍一遍地叫着母亲:
“仙娥啊!”
“仙、仙、娥。”
“仙……娥……”
回答父亲的是麻木般的沉寂。大地睡死了。村庄睡死了。母亲呢?恐怕也睡死了。
鸡叫了。鸡的翅膀将黑夜扇得发颤。鸡把大地没有叫醒,反而叫沉了。黑夜像阳光一样聚集在一起,压在了父亲身上。父亲爬起来,他一眼也没有看那院门,就离开了朱家庄。
回到家,父亲放轻了脚步。他从房子门背后摸到了那根续着麦穗头的麻绳,一只手提着绳子,一只手提着一颗钉子也没有钉进去的柴木凳子出了院门。父亲的脚下轻飘飘的,突然变得很亢奋似的,仿佛那绳子、那凳子就是鸦片,即使不吃,看一眼,也会剌激他的神经。父亲先在村子东边的那片洋槐树林里转了一圈,又犹豫不决地走出了那片树林,来到了村口的那棵大松树底下。
站在树下,父亲看也没看那遮天蔽日的树冠。他将柴木凳子放在树跟前,从从容容地踏上了凳子,站在凳子上将麻绳向树身上捆绑,他的动作干净而利索,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就像心中早已构好蓝图的设计师。父亲将绳子绑好之后,在绳子的两个头结了一个套子,然后,用手在套子上拉了拉,确信万无一失后,他拍了拍手,从凳子上下来,站在树下尿了一泡,畅酣淋漓地尿了一泡。然后,拉了拉衣襟,用手刨了刨蓬乱的头发,嘘了一口气,站上了柴木凳子,他将脖子伸进了绳套里,闭上了眼睛,只迟疑了一瞬间,便要伸脚去蹬柴木凳子,我在父亲的耳旁说,你不能那样。
父亲睁开眼睛时才发觉,他坐在树下。他用手摸了摸,他身子靠住的就是这棵大树。他自言自语“想死也死不了。真是老天爷不叫我死?”父亲似乎是历经了一场“死”之后刚活过来。他先是摸摸脖子,脖子上的绳索不见了,他又顺着脖子向下摸,当他摸到自己的胸脯、腿和脚时,证实了自己并没有死。他这才抬起头来看,朦胧的月光下,我的哥哥罗大虎站在他的身旁。父亲明白了,是儿子救下了他。那一夜,我的哥哥罗大虎儿乎没有睡。我不断提醒他,哥呀,你不能睡,你得注意父亲,你要盯住他。哥哥的心是和我相通的。他睡得很醒。父亲回家来,提着绳子走出院门之后,哥哥就尾随在他的身后了,迷迷昏昏的父亲没有觉察到。当父亲向身上挽绳索时,我的哥哥罗大虎竟然一时不知所措,直到父亲将绳索套进了脖颈,他才明白该怎么办。父亲手按住树身站起来,叫了一声“虎儿呀!”我的哥哥罗大虎扑过去,抱住了父亲,父子俩在树下哭抱成一团。松树上的松针似眼泪一样,纷纷向下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