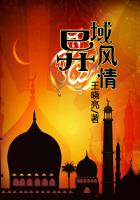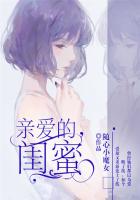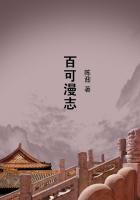十月初一是民间传统的祭祖节,又可称为十月朝或十月朔。关于它起源的学说很多,不论是周说、秦说,还是汉说,都印证了祭祖节的悠悠古风,而坊间的传说更是绵延千古而不绝。
在中国古代,人们多在农历十月初一祭祀祖先,给死去的宗亲上坟烧纸。同时,农历十月初一,也是进入寒冬季节的第一天,此后天气渐渐寒冷,这时,一家人都开始添加衣裳。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就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句,反映出当时的朝廷在岁寒之时便有赐衣之制。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也有朝廷赐衣之记载:“十月孟冬……朔日,朝廷赐宰执以下锦,名曰授衣,其赐锦花色,依品从效扫松,祭祀八坟莹。”由生者的御寒加衣,想到死者的防冷需要,从而觉得也应为在冥间的祖先送衣御寒。因此,祭祀时除了食物、香烛、纸钱等一般供物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供物——冥衣。在祭祀时,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寓意为已故的祖先送去御寒的衣服,叫做“送寒衣”。因此,中国许多地区以十月初一为“寒衣节”,又称“祭祖节”。
祭祖节起源的传说
据《荆楚岁时记》、《清嘉录》等记载,“十月一,送寒衣”的风俗是起源于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故事。
相传,秦时江南松江府孟、姜两家,种葫芦而得女,取名孟姜女,配夫范杞良。然而就在孟姜女新婚之夜,丈夫就被抓去服徭役,修筑万里长城。孟姜女日夜思念丈夫,悲痛万分。天气渐冷,孟姜女心想几年来丈夫的衣服早已磨破了,哪能敌得住塞外凛冽寒风,便决心给丈夫做身寒衣亲自送去。可是当她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长城脚下,却万万没有想到,丈夫范杞良在一年前的冬天,活活被累死,尸骨就埋在万里长城底下。孟姜女一听,不禁放声大哭。她边哭边双手拍打城墙,高喊着丈夫的名字,哭一阵惨死的丈夫,骂一阵残酷的暴君。在她愤怒的控诉声里,忽然间天崩地裂一声巨响,一段万里长城塌了,露出了丈夫的白骨。孟姜女守着白骨一连哭了七天七夜,之后将寒衣烧掉,只见那寒衣缓缓飘起,又渐下落,稳稳落下覆盖在白骨上。千百年来,这段忠贞爱情故事广为流传,而在山海关此故事流传最甚。
因此,长城内外便将农历十月初一这天,称作“寒衣节”。“十月初一烧寒衣”,也就成为北方凭吊已故亲人的风俗了。
祭祖节起源的学说
从科学意义上讲,关于祭祖节起源的学说可谓见仁见智,到目前为止,其主要有三说:
第一是秦朝说,据《荆楚岁时记》所说:“十月朔日,黍,俗谓之秦岁首。”即秦朝曾以农历十月为岁首,十月初一,正是新年之始。
第二是周朝说,其观点则对秦朝说提出质疑:秦统一中国的时间只有十余年,即使把太初改历以前的时间计算在内,也只有一百多年,秦岁首是否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值得怀疑。而周朝的腊日节在十月,据《礼记月令》可知,时值秋收完毕,地方官要亲自慰劳农人,让人们出猎禽兽,安排饮食,使农民得到休息。人们还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先祖和祭祀天宗、公社、门间的活动。后世的祭祖节,应该是周朝腊日节的遗俗。
第三是汉朝说,因为据《礼记月令》所说,十月是一年农事终了休息的月份,此时要进行宴饮冬祭。此外,又根据其他史书的记载,如《称衡别传》:“十月朝,黄祖在战船上宴会,吃黍嘴”;《后汉书张纯传》:“拾祭以冬十月,冬者五谷成熟、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也。”所以,祭祖节应产生于民间农时的节日,其时间大概是通行于汉代。
延伸阅读
十月祭蚩尤
人们之所以在十月祭尤,这与中国的古代历法有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十月为岁首。年末岁首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在这一个盛大的节日里,人们祭天、祭地,已约定成俗,但作为以军事吞并六国而称雄中华的秦始皇,在这个盛大节日里不仅要祭天、祭地,祭祀“兵主”尤也应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既然朝廷可以这样做,天下三十六郡当然都可以效仿,当时寿张县是尤的故乡,尤的后裔们便在十月岁首祭尤。东汉时期,洛阳也建起了尤。唐朝时期,仍保留着祭尤的习俗,李所著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中,保留着当时祭尤的全部祭文。从上述记载看,从春秋时期就有“兵”祭尤的习俗,到秦、汉逐步兴盛而形成习惯,一直延续到唐朝甚至时间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