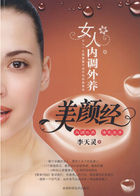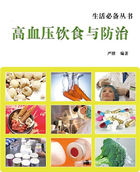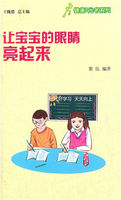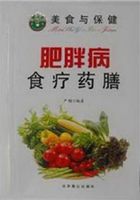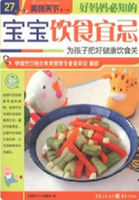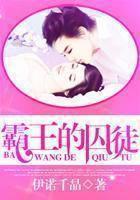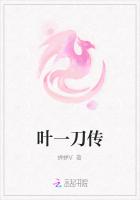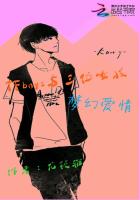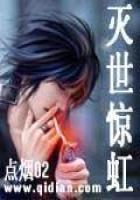痹证为经气受阻、孙络不畅、闭塞不通所致,多系外因结合内因而形成。缓者每遇气候变化或衣着寒暖失宜则易于发病,亦可变为急者;急者失治则陷于脏,内舍于心,缠绵难愈,或亦可变为缓者。因此,临床辨证,应认准病机变化,遣方用药,即不致误。
一、痹证血气辨
痹证在临床上基本分为两大类型。根据典籍,风寒湿痹命之曰痹证缓型;热痹命之曰痹证急型。缓证与急证何以得之,还有急转缓、缓转急,其病机何以变化之则是临床家应探讨之重要问题。
痹证缓型其病因《内经》早有论述,如《素问·痹论》篇说:“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这说明了风、寒、湿三种病因同时受之,即可得痹证。但据临证所见,凡两种病因同时受之亦可得病。如受风湿、受寒湿、受风寒即可得病者,则屡见不鲜。
风、寒、湿三气入侵确为致病之外因,但何以在同一环境、同一条件下,有病者,尚有不病者,其理何在?究其由则应归于患者个体经气之多少、气血之盛衰。正如《济生方·痹》篇中所说:“皆因体虚,腠理空疏,受风、寒、湿气而成痹也。”《儒门事亲·痹》篇中也曾指出:“凝水之地,劳力之人,辛苦过度,触冒风雨,寝处浸湿,痹从外入。”从这两段引文可以看出,一者认为“体虚”;一者认为“辛苦过度”,其共同认识均为风、寒、湿外因结合内因而发病的。其说含义正确,其指似不具体。我们认为,风、寒、湿三种外因侵犯人体之后,临证表现急型入于血脉;缓型入于经络。缓者之候,表现为肌肉、筋骨、关节等处之疼痛、酸楚、重着、麻木,甚之,关节肿大、屈伸不利等症,脉象沉涩。以证推因,以风为主者,证见肢体关节或肌肉疼痛,游走不定,故曰行痹;以寒为主者,证见肢体关节或肌肉疼痛剧烈,痛有定处,遇寒疼痛加重。有的皮下由于寒气凝结而有硬结,触之而痛,故曰痛痹;以湿主者,肢体关节、肌肉重着、麻木,活动不便,故曰着痹。即《素问·痹论》篇中所说:“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此三者均为经络之病也,大凡痹证缓型者,入于经络,经气强弱,决定受病与不病,故经气胜者则病轻,或不病;经气弱者则得病或病重。然而,经气的强弱则取决于脏腑的盛衰。一般来说肝、肾、脾最为重要,正如仲景所说:“寸口脉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为肾,弱即为肝。”又说:“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痛,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前者说明肝肾气血不足,后者说明脾虚湿盛。可见肝、肾、脾的盛衰与经气的强弱有着密切关系。因而认为痹证缓型者,病入于经络,入于经络者,一般病多不陷于脏。
至于痹证急型—热痹的产生,常因肺经素有郁热,多表现为口干舌燥,咽喉干痛,或皮肤丹疹等,如遇风邪入侵,常易隐于肺之孙络,入于血中,风血交争则高热弛张,汗出而热不除,如血虚则表现为低热,汗出津津。由于风入血中,风与血合,流注全身,因而血为风所燥,筋骨失血所养,故周身筋骨、关节疼痛、强直,即朱丹溪所指之“痛风”,脉象浮数或浮滑。《医宗金鉴》中曾说:“风在血中,则膘悍劲切,无所不至,为风血相搏。盖血主营养筋骨也,若风以燥之则血愈耗而筋骨失其所养,故疼痛如掣。”由于风胜热炽,迫血妄行,胸背及两臂内侧常易出现圆形红斑,然胸背为肺之外廓,两臂内侧为近临阴经所系。
因此,证系风邪入血之理,形成脉搏,即在预料之中,脉痹者最易内舍于心,舍于心则心悸、气短,动则怔仲,青少年为纯阳之体,风入血中,病变尤速,应更慎之。
此外,急型转化缓型者,比比皆是;缓型转化为急型者,亦属不少。究其转化机理,风寒湿痹——缓型为病邪入侵经络,郁久化热,入于血中则热势作矣。《证治类裁·痛风》中说“寒湿风郁痹阴分,久则化热攻痛。”亦有重感风寒之邪,阳多阴少而表现为热痹者,如《金匮翼》说:“脏腑经络先有蓄热,而复遇风寒湿气客之,热为寒郁,气不得通,久之寒亦化热,”故成热痹。
反之,急型痹证——热痹,治疗得当,可以不变为缓型痹证;如治疗不彻底,虽热势已退,肌肉关节疼痛大减,常易由急型转为缓型。此种情况,乃急型痹证经用清热、除风等治疗,将血中之风赶入经络而成缓型,少有风、寒、湿外因,证候即可表现为肌肉、关节缓慢疼痛、沉重、麻木反复出现而为痹证缓型。缓型常有数年或数十年而不能根除者,故急型的治疗尤其重要。
风寒湿痹证(缓型)虽证在经络,实为肝、肾、脾虚,而肝肾不足则由脾气不充所致。因此,补气以固脾虚,养血以滋肝肾,乃固本之理,除风、燥湿、通络、止痛乃因证而设。刘茂甫教授家传秘方——刘氏黄芪赤风汤即按此意创制而成,经三代应用随证加减,效果颇为满意,该方被选入西安医科大学1972年编印的《常用药物手册》中,其组成黄芪、当归、赤芍、防己、防风、威灵仙、桂枝、牛膝、木瓜、伸筋草、透骨草。如为行痹者,加羌活、独活;痛痹者加干姜、乳香;着痹者重用防己,并加薏苡仁。此方黄芪以补脾气,当归、赤芍以养肝肾,防风、威灵仙以祛风,防己、木瓜以除湿,桂枝、牛膝、伸筋草、透骨草以通络止痛。
至于热痹——急型乃肺热入脉,风入于血,常易成为脉痹,最易内舍于心,急应以甘寒清热,苦寒解毒,佐以解肌之剂,如《金匮要略》中之白虎加桂枝汤,此方虽属效甚,但对此证还不能丝丝入扣,欲求速效,应在此方基础上加上述治则所用之品,诸如宜加苦寒之大青叶、黄芩;宣肺之杏仁,桔梗,周身强直困痛,可重用防己并加木瓜,更宜加入红花、丹皮、赤芍,所谓“治风先活血,血活风自灭”。服上方后,热势消退,身痛大减,还须再进十余剂,巩固疗效,以防生变,内陷舍心。
总之,风寒湿痹(缓型)的治疗除祛风、燥湿、通络、止痛之外,必须兼以补气养血为要;热痹(急型)的治疗,除甘寒清热、解肌佐以苦寒解毒、宣肺之外,更须注意活血通脉为先。
二、痹证缓急辨
刘茂甫教授对痹证的治疗效果,为患者所称赞,他的经验是:痹证有缓急之分,但二者又可互相转化。缓者每因气候变化或衣着寒暖失宜而复发,亦可变为急者;急者失治则可隐于脏,内舍于心,缠绵难愈,或亦可变为缓者。因此,临床辨证,掌握病机变化,遣方用药,即不致误。可将风寒湿痹命之曰痹证缓型;热痹命之曰痹证急型。
痹证缓型多以风、寒、湿三种邪气,同时受之,为致痹之因。据证所见,凡两种病因同时受之亦可得病。如受风湿、寒湿或风寒即可得病者,屡见不鲜。
风、寒、湿邪,侵犯人体之后,急型入于血脉;缓型入于经络。缓者之候,表现为肌肉、筋骨、关节等处之疼痛、酸楚、重着、麻木,甚者关节肿大,屈伸不利,脉象沉涩。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此三者均为经络之病也。大凡痹证缓型者,入于经络。经气强弱,决定受病与不病,故经气胜者则病轻,或不病;经气弱者则得病或病重。然而,经气的强弱则取决于脏腑的盛衰。一般来说,肝、肾、脾最为重要。痹证缓型者,病入于经络,入于经络者,一般病变多不陷于脏。
至于痹证急型——热痹的产生,常因肺经素有郁热,多表现为口干舌燥,咽喉干痛或皮肤红斑等,如遇风邪入侵,常易陷于肺之孙络,入于血中,风血交争则高热弛张,汗出而热不撤,如血虚者则表现为低热,汗出溱溱。由于风入血中,风与血合,流注全身,因而血为风所燥,筋骨失血所养,故周身筋骨、关节疼痛、强直,脉象浮数或浮滑。由于风盛热炽,迫血妄行,胸背及两臂内侧常易出现环形红斑,此为脉痹。脉痹者,最易内舍于心,舍于心则心悸,气短,动则乏力。青少年为纯阳之体,风入血中,病变尤速,应更慎之。
有急型转化缓型者,亦有缓型转化为急型者,究其转化机理,风寒湿痹为病邪入侵经络,郁久化热,入于血中热势则作。反之,热痹,治疗得当,可以痊愈,如治疗不彻底,虽热势已退,肌肉、关节疼痛大减,常易由急型转为缓型。此种情况,乃急型痹证经用清热、除风等治疗,将血中之风趋于经络而成缓型,少有风、寒、湿外因,表现为肌肉关节缓慢疼痛、沉重、麻木反复出现。缓型常有数年或数十年而不能根除者,故急型的治疗尤为重要。治风寒湿痹应补气养血,疗热痹应注意活血通脉。
风寒湿痹证(缓型)虽证在经络,实为肝、肾、脾虚,而肝肾不足则是由脾气不充所致。因此,补气以培脾虚,养血以滋肝肾,乃治本之法。除风、燥湿、通络、止痛乃因症而设。家传秘方——刘氏黄芪赤风汤即按此意创制而成,经三代应用其疗效颇为满意。其组成为黄芪、当归、赤芍、防己、防风、威灵仙、桂枝、牛膝、木瓜、伸筋草、透骨草。如为行痹者加羌活、独活;痛痹者加干姜、乳香;着痹者重用防己并加薏仁。此方黄芪以补脾气;当归、赤芍以养血活血;防风、威灵仙以祛风;防己、木瓜以除湿;桂枝、牛膝、伸筋草、透骨草以通络止痛。
至于热痹(急型),因肺热入脉,风入于血,常易成为脉痹,最易内舍于心,应急以甘寒清热,苦寒解毒,佐以解肌宣肺,更应治以活血通脉。一般常用甘寒清热兼以解肌之剂,如《金匮要略》中之白虎加桂枝汤。此方用于热痹尚不属丝丝入扣之方。欲求速效,应在此方基础上加上述诸品,诸如苦寒之大青叶、黄芩;宣肺之杏仁、桔梗;周身强直困痛,可重用防己并加木瓜,更宜加入红花、丹皮、赤芍。服上方后,热势消退,身痛大减,还须再进10余剂,巩固疗效,以防生变,内陷舍于心。
总之,风寒湿痹(缓型)的治疗除祛风、燥湿、通络、止痛之外,必须兼以补气养血;热痹(急型)的治疗,除甘寒清热解肌佐以苦寒解毒、宣肺之外,更须注意活血通脉。